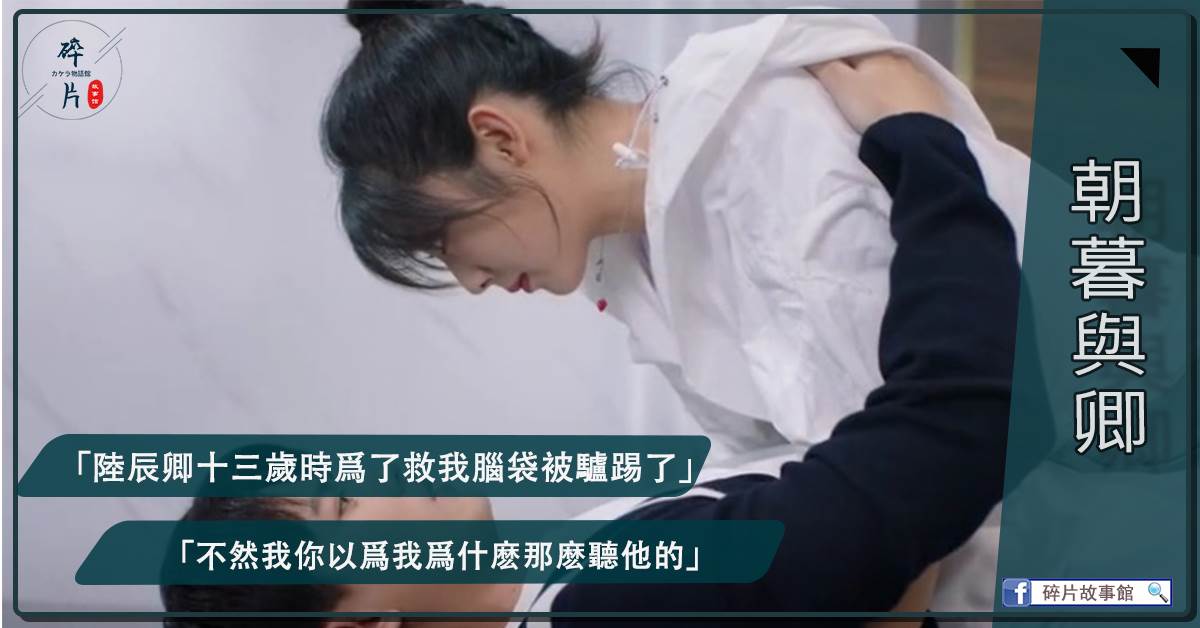《朝暮與卿》第3章
敏感的失主再加上一堆人煽風點火的分析,她現在幾乎已經斷定我是心虛不敢回。
我仔細回憶了下當天,那是和陸臣卿同節課,不出意外的話,我應該是跟著他一起走出門的。
因為要幫他拿衣服。
我就在群里說,我不是最后一個出門的,我和陸臣卿一起。
失主看見我這麼回了也只好作罷,圍觀看熱鬧的人散了也都散了,然后陸臣卿突然在群里跳出來,說了句。
「我沒跟你在一起。」
看見這句話的時候我就突然想起,他曾笑著跟我說,叫我不要后悔。
我愣愣地看著手機屏,彈出了一條又一條的消息。
失主以為我撒謊了,抓著我不放,要我跟她去趟導員辦公室。
籃球社社長的發言也很巧妙,說什麼「我就講我沒有看錯啊」,陸臣卿自發了那句話之后就沒有出現。
甚至群里已經開始有人叫我道歉。
一股由心底忽而彌漫的慌亂一下席卷我,就像是突然被人扣下什麼罪證,而我還不知該由何解釋起。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就是和陸臣卿一起出門的。
他晚上要打籃球,我幫他拿水拿衣服。
他記憶力一向好,我不信他能忘。
也就是說,他故意的,把事情鬧大,想看我的丑態。
8
我不記得陸臣卿是從什麼時候,那麼喜歡捉弄我的。
先開始只是小惡作劇,而后越來越變本加厲。
有個響徹蟬鳴的午后,他故意給錯了我地址,讓我在烈日炎炎下找了他兩個小時。
我找到他的時候,他坐在學校操場的欄桿上,身后的藍天白云,琥珀色的瞳孔里倒映出氣喘吁吁的我,嘴角勾了個微妙的弧度。
ADVERTISEMENT
「為什麼非得跟著我?」
我覺得他那時候的笑,太燦爛了。
「因為你救過我,陸臣卿。」
剎那間,他的笑容又消失了。
他知道自己十三歲的時候為了救我腦袋被驢踢了,也知道我一直跟著他是因為什麼。
他的手里一直握著一瓶礦泉水,我剛開始沒注意,直到他擰開瓶蓋,水流順著我的頭頂澆下。
打濕了頭發和衣服。
三伏天里其實并不冷,甚至有那麼一絲涼意,我站在原地,覺得自己這樣大概還是太狼狽了。
「現在你還要跟著我嗎,嗯?」
明明他聲線懶散得要命,可話說出來卻那麼惡劣。
我在心里不斷跟自己說,陸臣卿做手術做了一天一夜,如果沒救回來,那他現在這條命,就該是我背。
可我還是沒來由地顫抖了下,大概是涼水流入了后頸。
那天晚上,我發燒了。
估計是前幾天就有點小感冒,再加上穿著濕衣服回家,燒起來的溫度并不高,可讓人渾渾噩噩的。
我在被子里吸鼻子,吸著吸著就哭了,我想大抵是發燒太難受了,或者我沒有想象中那麼堅強。
我欠陸臣卿。
我打算拿我的十年去償還,這期間他對我做什麼都沒關系,因為我欠他。
我欠他的。
9
我回來神來的時候,學長已經在我身旁就著我的手把聊天記錄全看了個遍。
「c 樓的事兒?」
我點點頭。
「你偷的?」
他勾著唇角笑了聲。
我知道他在開玩笑,可我現在才瞧見他的眼眸是桃花型的,笑起來總平白多了股風流。
「走吧。」他突然調轉了個方向。
「去哪?」我追上他。
「去找你們級的導員,既然陸臣卿不愿意幫你作證,我幫你作證好了。
」
「……學長。」
「嗯?」
他回頭看我,眼里落了道巷子里斑駁的光。
「作假證不好,我知道。」
10
其實這事兒就算是真鬧到導員那,也不可能草率地解決。
我聽說警察已經介入了,群里那風波也不了了之,當然,陸臣卿明知道可以為我作證還故意將臟水往我身上潑的事兒,我算是記住他了。
我真的挺生氣的。
之前的每一次生氣我都忍了下去,但這次不可能,我去了他最近經常去的學校旁邊的那家網吧,我知道他肯定在那。
我連他常占的機位都知道,不過今天那臺機子位置上的人不是他。
我本以為會無功而返,結果在網吧門口的墻角撞見了他。
他本來叼了根煙,打火機亮起的微光轉瞬即逝,他卻把煙和打火機收回口袋里了。
「什麼事兒?」他低著頭問我。
「我每周五哪次不是陪著你上完最后一節課?為什麼說那天沒看見我。」
「是啊,你哪次不是陪著我?」
他的重點怪怪的,嗓音比以前要啞。
「這次為什麼不陪了?」
「……我為什麼非得陪你。」
我退后了幾步,他就抵著我上前。
面前的人有些陌生,他的頭發好像變長了,一些碎發遮住了晦澀的眼睛。
「你不是說欠我嗎?怎麼,還完了嗎?」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什麼話來。
「林子暮,那天……誰知道呢?我早就忘了,說不定單單那天你沒跟我一起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有問題。」
他指了指自己的腦袋。
「畢竟我把十三歲之前的事全忘了,再忘掉一兩件小事,也不過分吧?」
「那你該去醫院看下腦子了,陸臣卿。」
我皺著眉,想推開他。
他擋住了我的路,接連亮起的燈光為他的輪廓勾了個金色的邊,他的眼眸里洶涌著一些我看不懂的東西。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