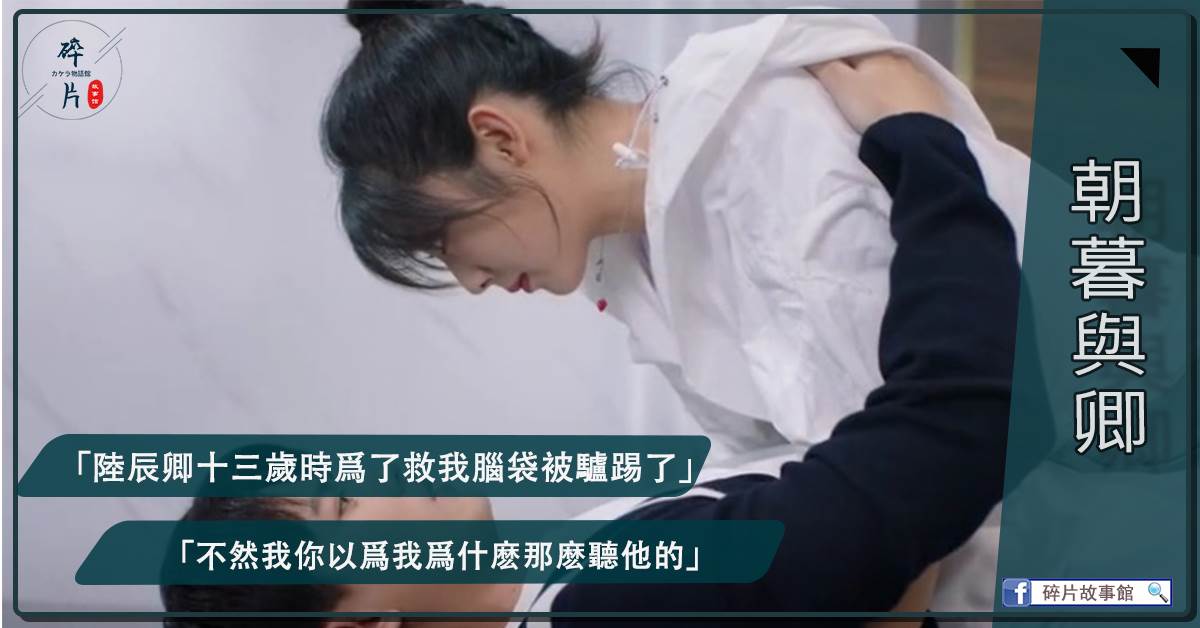《朝暮與卿》第8章
」
「林子暮,你別……」
他的聲線里的慌亂,我聽得多清晰啊。
電話那頭的人還想再說什麼,可有人從我耳邊拿走了手機,替我把電話掛了。
只閃著一盞路燈的黑夜里,他的眼睛里卻有破碎的光。
學長把我拉進了懷里。
太溫暖了。
或許是晚風太冷。
他的聲音依舊清散,帶著碎得不成樣的寂然。
「逃到什麼地方去吧,林子暮。」他說。
17
我從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逃。
天地廣闊無邊,可黎明連前路都是昏昏暗暗的。
車換給學長開了,開得挺慢,我又有些疲倦,迷迷糊糊地倚著座位睡,再醒來的時候,四周是漫無邊際的曠野。
風揚起野草晃動,黎明的星光輪換。
「我們去哪?」
他的車停在一棟二層的建筑前,建筑在一片開闊的平地之上。
「去天上。」
「去天……啊?」
「林子暮,你恐高嗎?」
「還行,學長,我們……」
他自然而然地牽起我的手腕,往建筑里面走。
「這是家跳傘俱樂部。」
……
時針才劃過四點,俱樂部的一層已經有人在等著,他好像和學長很熟,朝著他挑了挑眉。
「你來得真巧,正好馬上第一班次。」
學長打了個哈欠,拉著我在他對面的沙發坐下。
「我掐點來的。」
男人好像注意到了我,朝我笑了笑。
「你女朋友?」
半晌,沒回應。
我剛想解釋,學長突然輕輕嗯了聲。
他坐在我身邊,所以我聽得很清晰。
我知道有的時候是沒必要做過多的解釋,可那麼坦坦蕩蕩地承認,我還是不自在。
連帶著沉寂一晚的心臟又如同復蘇般狠狠跳了下。
……
我第一次跳傘。
可學長好像已經是老手,他幫我穿好馬甲,在扣我身后的扣子的時候,手存在感很強地抵在我的后腰。
ADVERTISEMENT
我想找點話打破這會兒的安靜。
「我們跳多高呀,學長。」
他沒說話,手指上的力量卻不知怎麼透過我的尾骨傳到了全身。
「有跳死的可能嗎,學長?」
「……」
依舊不說話。
「學長??」
他嗯了聲。
「等我弄完你后面。」
……本來這句話,其實沒什麼。
可好巧不巧我們剛才在一樓見到的那個男人抱著頭盔路過我們,還頗為戲謔地笑了幾聲。
那句話,瞬間就變了味。
偏偏學長弄完直起身攏住我的頭發,湊到我耳邊,說的正正經經。
「耳尖紅了,林子暮。」
嫌不夠似的。
「……」
我們跳的四千米。
而且是日出跳,跟我們一個直升機的男人說今天特別趕巧,這種景色對客人來說每次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直升機轟隆隆的聲兒特別吵,學長因為要帶著我跳,所以我幾乎是坐在他的懷里。
馬甲有搭扣,將我們緊緊拴在一起。
說不上是第一次坐直升機往四千米的高空飛更緊張還是馬上要和這個男人一起跳下去更緊張,反正到了這時候,心臟的跳動聲連我自己都聽得清。
可是忽而之間,窗外的景就擁進我的眼眶。
我從沒見過于地平線升起的艷陽,廣闊無垠的藍融進璀璨的金黃。
向著很高很高的地方升去,連云層都捱于身下,天邊的光弧躍進眼底,光燦爛到仿佛這一輩子都見不到。
有人在三千米的時候跳了下去,朝后躍去的時候跟我們比了個大拇指。
而后是四千米,直升機的門打開的時候,風便一股腦地灌了進來,學長從身后給我戴上護目鏡。
「害怕嗎?」
因為風聲特別大,他干脆在我耳旁說話。
我搖了搖頭。
主要是,綁都跟他綁在了一起,我沒得選。
跟我們一道的男人因為是單人跳傘,所以比我們要先跳,他從直升機旁的欄桿扒著跳了下去,成功地耍了個帥。
然后,終于到了我們。
當他摟著我坐在飛機門的邊將要向下跳時,他好像對我說了什麼。
可我沒聽清,腳下是浩瀚的云海,風從耳邊呼嘯而過,我大概只知道他叫我握好背帶,然后就這麼帶著我向后跳了下去。
那是我這輩子看見過最好看的天空。
直升機就這麼快速地從我的視線之中消逝,他帶著我在空中翻了過來,向下看時是無邊無際的山川和河流,如同一道耀眼金邊的光弧環繞著那廣闊無際的天。
太陽自地平線上升起,霞光染上一望無際的橙。
連高呼都聽不見,只是覺得那一刻就這麼墜落下去就好,摔進山河的懷抱,或者就此在黎明前燃燒。
他還真就帶我逃到了個誰也去不了的地方啊。
從四千米的地方跳下去,真要說,就是一眨眼的事兒。
特別快特別快,打開降落傘之后從沒想過這趟旅程就這麼結束了。
可腿還是發軟,落地后他幾乎是半摟著我被我壓在地上。
沒了風聲,他的喘息就響在我的耳邊。
「做我女朋友吧,林子暮。」
他摘下我的護目鏡,把我的頭發勾在我的耳后吻我。
18
「暮暮,你是不是和陸臣卿鬧別扭了?我看你回來,都沒找過他。」
阿歡是我發小,放寒假回到老家后,這塊朋友便往來著串門。
大概是我這次回家太過反常,不僅沒有追著陸臣卿一起回,而且陸臣卿來找我我全回絕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