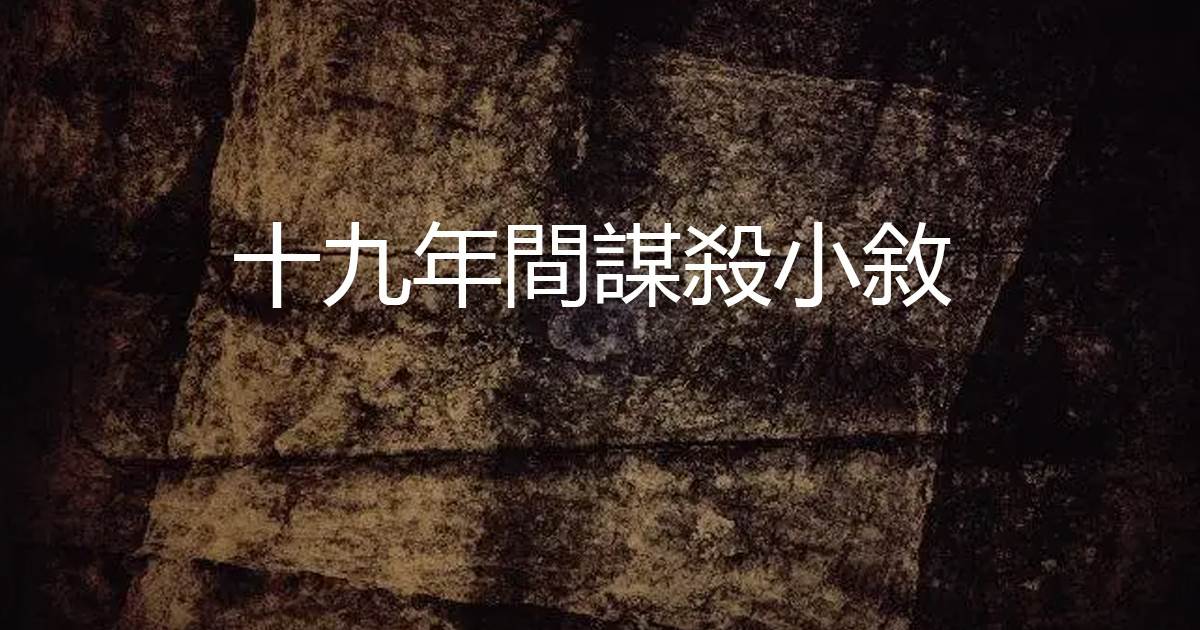《十九年間謀殺小敘》第29章
“有點失眠。”她又喃喃重復了一句。但為什麼失眠呢,該怎麼說呢,神經衰弱嗎,為什麼會神經衰弱呢,都過得這麼幸福了,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她說得出口嗎?
“你有事情憋著啊。”郭慨指指她的心口。柳絮被他這麼一指,許許多多的東西克制不住地從心底里翻起來。她心里叫著糟糕糟糕,但眼淚已經止不住地流了下來。她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自己卻根本沒有留意到這點。
“我有過一個孩子。”柳絮說,“沒人知道,其實我在婚禮那天喝了酒。是我殺了她,這是我的報應。”
她開始談這個孩子的事,開始懺悔,這件事已經在她心里憋了很久,連費志剛也不知道婚禮時她喝過酒。而在那之后,她再也沒有能懷上過。
郭慨只是在旁邊聽著,他知道柳絮只是需要一個樹洞說說話。等柳絮停下來的時候,臉上的眼淚已經干了。
“現在感覺好多了?”郭慨問。
“謝謝你。”柳絮說,“你真是個好人。”
郭慨苦笑,“你從前可不是這麼覺得的吧。”
“但你是怎麼看出我不開心的,有那麼明顯嗎?”
“你先前說的那些,公益、運動、心理學。這麼多能調節心情的事情,你每一樣都那麼拼命去做,太辛苦了。我終歸做過刑警,基本素養還剩下一點。”
柳絮沉默了一會兒,說:“其實這些年我過得很糟糕,并不僅僅因為那個孩子。我以為辭了職待在家里,一切會慢慢變好,時間會把記憶帶走,把她帶走。你知道那時我為什麼辭職嗎?”
“聽說……是出了醫療事故,因為暈血?”
柳絮搖搖頭,“記得我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摔進尸池住院,你來看我的事嗎?”
ADVERTISEMENT
“當然記得。”
又是長長的沉默。然而她終于下定了決心。
那陰影一步步迫近,就快要把她吞噬。做錯了事就要付出代價,但這代價實在太過流重,四年前的醫療事故是報應,和父親決裂是報應,小孩流產也是報應,柳絮甚至有預感,她這一輩子都不會再有孩子了,自己這樣一個坐視好友被毒殺的人,是不配當母親的。然而她終究是渴望有一個人能安慰自己的,在心底里,柳絮隱約曉得,對面這個男人,大概是除了母親之外,唯一一個在知曉了全部事情之后,不會指責她的人。
“那時我應該對你說的。如果說了,事情應該會不同。”
于是柳絮開始說文秀娟的事。她打開了那個閥門,陰寒的氣息從心底的黑洞中吹出來,讓她一陣一陣地發冷,說到后來,整個人都發起抖來。她的神情讓郭慨為她擔心,他握住她的手,那手冷得像冰,讓他覺得自己無法溫暖她。柳絮的手被包裹住的時候,心頭跳了一下,她知道郭慨并沒有別的意思,甚至她覺得手被這樣握住,心里多少安定了一些。
但這總歸不合適。
可是抽出來又顯得不禮貌了,或許再稍稍停留一會兒。她有多少時間沒感覺到安定了,哪怕只有一絲一毫,這讓她有些依戀。柳絮想到了費志剛,臉燒起來,這是因為自己最大的秘密被他知道了,才會有的特殊情緒吧,并不意味著別的,只是情緒宣泄后的副作用,柳絮用她僅有的一點點心理學知識胡亂分析著。
郭慨松開了手。
“交給我吧。”他說。
“啊?”
“我來查。”
柳絮嚇了一跳。她只是傾訴一下,但郭慨居然……她忽然意識到,這就是郭慨啊,他還是那個人。
“可是事情已經過去那麼多年。”
“還在刑事追溯期內。有機會的,至少,嫌疑人的范圍就這麼大,我一定能把他抓出來。柳絮,你的病根在那兒,如果不去管它,一輩子你都不會開心的,得把這根刺拔掉才行。還你朋友一個交代,也還你自己一個交代。”
柳紫傻傻地瞧著郭慨,又有些想哭。當年如果告訴他,該有多好,她再一次這樣想。那時候,自己真是太小了。
郭慨沖她笑笑,“感動個啥,別瞧我說得好聽,其實你知道我這幾年戶籍警當得有多無聊嗎?丑話說在前頭,我只能業余去查,進程不會太快,你呢也別著急。這樣,我們每星期碰個頭,我向你匯報進展。”
柳絮還能說什麼,只有點頭。
接下來郭慨詳問了當年的諸多細節,記在隨身的小本子上,直到天色暗下來,才道別離開。
臨走,已經走到了店門外,郭慨對柳絮說,其實這些年我常去你家的。柳絮嗯了一聲。郭慨又說,你爸爸他年紀大了,背也駝起來了。柳絮不說話。最后郭慨說,其實你結婚那天,我和你爸一起去的,只是他沒進酒店,就站在對馬路那兒看著。柳絮怔征出了會兒神,然后嘆了口氣。
2
柳絮醒來的時候,看見文秀娟在旁邊專心地瞧著她,烏黑的長發蔓延過兩只枕頭間的空隙。
你去圖書館嗎?柳絮問。
哦對了,你已經死了
能告訴我是誰殺了你嗎?哦對了,你也不知道。
長發漸枯。
柳絮忽地又看不見文秀娟的臉了,她好似并沒在看著她,而是把頭埋在枕頭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