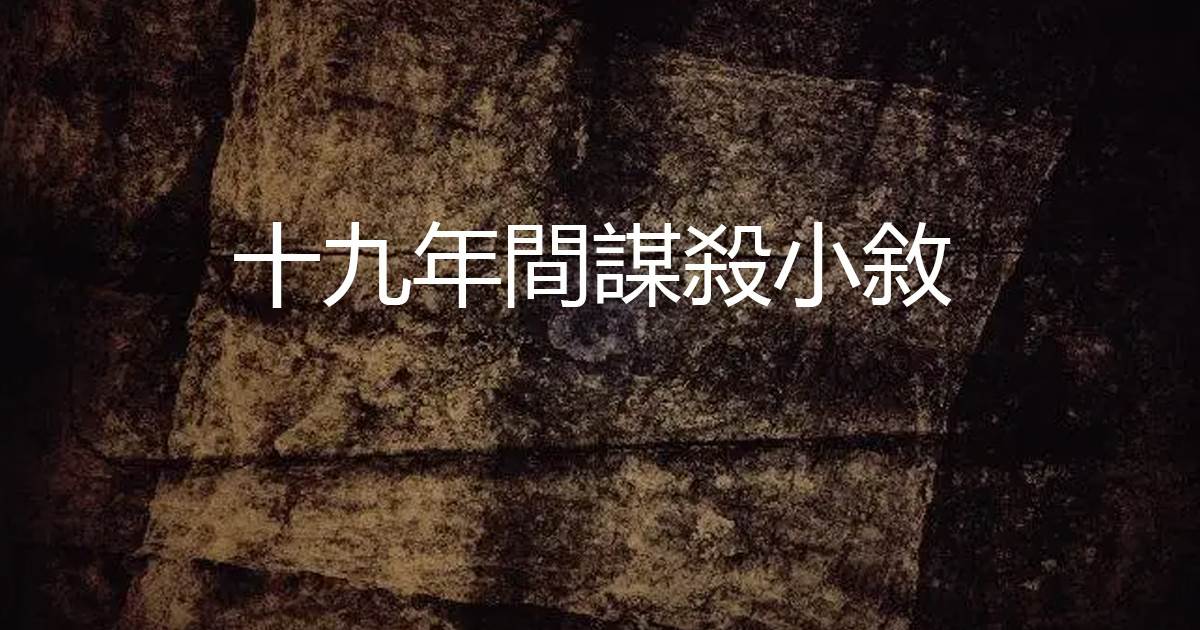《十九年間謀殺小敘》第66章
現場幾個同學心里都堵得難受,但也沒人會傻到跑上去和輔導員理論。
而就在昨天一大早,文秀娟把用涼水冰了一晚的兔子阿白上交給了軍訓班長。班長特別貪吃,早就說過與其養著兔子浪費蔬菜不如吃掉的怪話,聽文秀娟說兔子受傷大出血死了,便高高興興把兔子給了炊事班中午加菜。這事兒,好巧也有同學看見了。
如此一來,同學們看教官和輔導員的眼神都變得有些異樣,在委培班這些同學的心里,教官輔導員和文秀娟,都是一路人了。
自始至終,都沒有人告訴軍訓班長和輔導員,文秀娟對兔子做過些什麼。
項偉佩服得不得了,明明已經搞到群情激憤,那麼惡劣的處境,文秀娟硬是把老師拉到了同一條戰壕里。如果真有人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金浩良,想必文秀娟也就徹底被打入別冊另眼相看了。別說班長的頭銜,搞不好會進甄別黑名單呢。
這樣,他就和文秀娟共享同一個秘密了。一個好的開始,項偉這麼覺得。
3
文秀娟一點一點地往上爬,她看到些微光,覺得自己就快要爬出來了。軍訓未尾的那檔子事情,讓她光環褪盡。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無論她有多努力,表現得多優秀,大家都覺得她是個不擇手段,不可深交的人,甚至她找到全班成績最糟糕的馬德,提出和他互助學習,想幫他離開甄別區,都被拒絕了。
有時候,文秀娟覺得,還好有一個項偉。如果不是他,自己應該已經不是班長了。
ADVERTISEMENT
對文秀娟來說,被孤立的感覺并不陌生,但有一個可以共同陪伴的人會讓日子好過許多。
幫她占位,幫她打飯,幫她的寢室打熱水,幫她張羅班務。這些幫助對文秀娟可有可無,但如果她拒絕接受,也就等于拒絕了和其他同學的潤滑空間。項偉從未曾真正表白,但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心意所在。一些時候,文秀娟覺得這樣也不錯,一些時候,她會問自己,還要這樣多久。項偉總是要表白的,那時她應該怎麼辦?平心而論,項偉真的不錯,可她不想要這麼個知根知底的人,她所做的所有事情,不正是為了從老街這個泥沼里爬出去麼。她希望能有一個與她身份相匹配的男人——她那個法租界大家族的身份。只是,她能做得到嗎,她的面具可以足夠好到永遠不被揭穿嗎?每當這樣懷疑自己的時候,下一刻,她就打足精神,全力以赴去做好手上的事情,不管怎麼說,領先別人一步總沒錯,在目之所及的范圍內。
也許正如哲學課本中所說,事物是螺旋上升的,并沒有事事領先的道理。文秀娟的凡事拼命,讓她在第二學年快結束的時候倒下。校運會那天下雨,她報的是女子四百米接力,棒交到她的時候,雨大得眼睛都睜不開。她已經覺得有點兒不得勁,但集體榮譽是讓她挽回印象分的好機會,所以拼命跑了個第一。跑完發現月事來了,然后就高燒病倒。她躺在寢室里,迷迷糊糊的時候想起往事,這光景和姐姐那一場高燒好像啊。
撐了幾天還不見好,咳嗽越發厲害,再去醫院查的時候轉成肺炎了。
到五月中,她已經在家休了兩個星期。這天她從醫院吊完點滴慢慢騎著車回家,感覺力氣比前幾天回來些,應該就快能重回學校了。文秀娟騎在熟悉的街道上。她從小在這里長大,閉上眼睛,一樣能看見老街城池般在面前升起來,看見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以及那些個死了又活的貓貓狗狗。有生以來,老街一成不變,同樣的風景和同樣的人。文秀娟痛恨這樣的一成不變,外面的世界在怎樣劇烈地變化著啊,再有一個多月,香港都要回歸了。
經過水果攤的時候,阿文叔說有人在找你啊。文秀娟問是誰,阿文叔笑笑,說不認得,又笑笑。文秀娟隱約覺得不妙,跨上車緊蹬了幾把,拐過兩個彎,蹚過窄巷,便瞧見了項偉。
項偉手里提了袋梨,站在文家矮檐下,望見文秀娟回來了,招手沖她笑。
文秀娟一個剎車,整個后背都涼了,她仿佛聽見了世界的斷裂聲。遮羞布被掀開了,是的,項偉當然知道自己是誰,自始至終,他都知道,她就是老街那個泥地里的姑娘,出租車司機和癱子的女兒。
一步一步,文秀娟推著車朝自家門口走,她不能停不能逃,那是她的家,是她還沒能割斷的根,又能逃到什麼地方去。項偉已經在這里了,圖窮匕見,她只好面對。前年軍訓時見到項偉,她就覺得天要塌了,去年春夜里被司靈抓到給兔子開刀,她也覺得完了,卻都闖了過來。
這一次要如何?
項偉見文秀娟慢慢走過來,面無表情,只以為她是病著,疲倦了。他哪里猜得到文秀娟心里轉的這許多念頭,兩個人的關系在他看來,是心照不宣的了,文秀娟病了這許久,他來探望一下,難道不是應該的麼。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