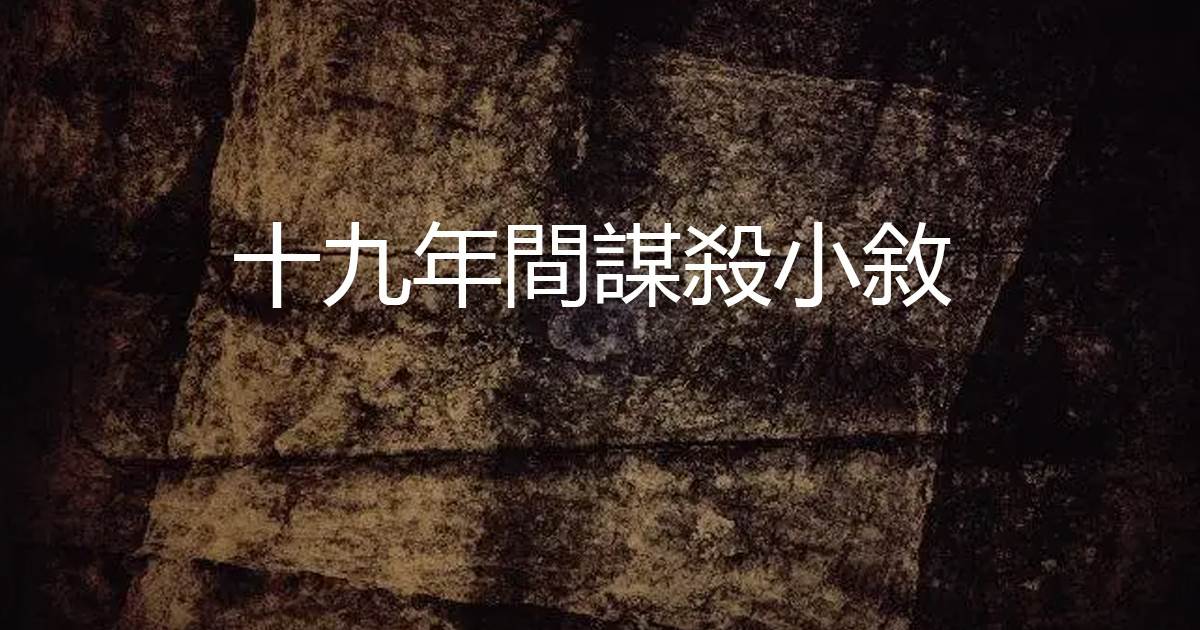《十九年間謀殺小敘》第68章
他嘆口氣,叮囑了幾句就離開了。這里是寢室樓入口,來來往往不少同學,他要帶好班級,也得考慮同班大多數人的感受,不方便表現得與文秀娟過分親密。
文秀娟自問,我還能做什麼?
這兩天她確實四處奔走,做了所有能做的事。她看起來活脫脫像一個為男友擔優焦慮的女人——如果項偉作弊不是她告發的話。這些舉動毫無用處,也不會為她在同學間賺得一點點同情分,要是委培班不甄別作弊的項偉,反倒去甄別別人,放在哪兒都說不過去。倒是被她陳情的老師們,都愈發地喜歡這個孩子。但這些對文秀娟都不重要,她只想一件事,要怎麼讓項偉好受一些。
項偉這些天幾乎足不出寢室,仿佛只在等待最終的審判結果。他沒有試圖聯系文秀娟,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卻也顯得理所當然。今天,甄別名單正式確認,雖然還未公布,但也不算什麼秘密,項偉不曉得知道這個消息沒有。文秀娟覺得,她做的這些事情想必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她去寢室里找他,要怎麼說話,第一句話得是什麼語氣?會不會立刻就被趕出來?要怎樣才能讓項偉理解她當時的慌急無措?興許什麼都不說,抱著他哭一場?
身邊不知不覺間聚攏了一群同學,往樓上指指點點。文秀娟一激靈,下意識去看三樓的那扇窗戶,并沒有人。她又繼續往上看,四樓、五樓,在五樓樓頂天臺上,瞧見一個熟悉的人影。
所有的血都涌上了腦袋,文秀娟想都不想就往里沖,一步三個臺階地在樓梯間跑,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周圍的一切都是急速旋轉而模糊的,光線越來越暗,直到看見五樓頂上那扇小門透出的傍晚的光亮,仿若天堂之門。
ADVERTISEMENT
她從門里沖出去,好像在天臺上看見了一道幻影,一轉眼卻又空空蕩蕩,她直直往天臺邊緣跑過去,就像那次四百米接力的最后一棒,拼盡了全力,直到肚子重重撞在水泥護擋上,上半身向外彎折,雙腳幾乎離地要往外翻出。她大半個身子懸在虛空,低頭往下看,耳朵里轟隆隆地響,聽不到任何其他聲音,一瞬間世界于她是沸騰而無聲的,她仿如見到了萬花筒旋起的某一刻,底下的人群星星點點向一個中心圍攏過去,周圍繽紛的碎片和整個世界一起分崩離散。
五、羔羊
1
文秀娟坐在松樹林邊吹簫。吹的是《陽關三疊》,一曲吹罷,她把簫擱在膝上,想要平心靜氣,害怕卻止不住地從心里涌出來。
文秀娟一直覺得有人要害她。她和文秀琳一起顛沛在這個世界,沒有領會過母愛,寥剩不多的父愛也須與人分享。自從被阿姐背叛,她更是深切地體會到了世間的惡意,她努力跑在所有人前面,想要有更強大的力量,來抵擋這惡意。項偉被甄別后,委培班同學對她的惡意,濃烈得如同實質。暑假休了不到一個月,新開學的時候,每個人都在用眼神對她說“你怎麼不去死”。她半夜里會想,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她的睡眠變得很差,上課注意力也不容易集中,有時候身體的某處還會有來無影去無蹤的疼痛。她知道這應該是神經痛,壓力太大。
吹簫其實對身體是有好處的,這需要很強的氣息控制,而氣息訓練自古就是各種養生學里的重要一環。
可是今天吹奏過程里,好幾次她都覺得氣要接不上來,不得不把氣息減弱,搞得簫聲軟綿綿像受了潮的蛛絲,一些精細巧變的音節都沒有足夠的氣息去吹奏表現出來。
我這是怎麼了,文秀娟問自己,隱隱約約地不安起來。
坐在旁邊的柳絮聽不明白好壞,只覺得簫聲悠遠,此刻夕光漸斂,分外有送別的古意,不由輕輕鼓起掌來。風過松林,柳絮打了個寒戰,心里又埋怨起自己的膽小來。
回到寢室門沒鎖,里面卻一個人也沒有。寢室里其他人總是抱團活動,非但把文秀娟排除在外,也時常忽略了和文秀娟走得極近的柳絮。文秀娟猜想,柳絮這個傻姑娘應該覺出點什麼了吧。
到九點多,司靈她們說說笑笑推門而入,柳絮從床上探出頭去,說回來啦,你們去哪兒玩啦?司靈嘻嘻一笑,說和影像系聯誼去啦。琉璃說本來想叫你呢沒看著你。柳絮稍有些遺憾,想多問兩句,忽然覺得有些不對勁,文秀娟怎麼沒聲沒息的?
文秀娟正背對著柳絮站在長桌邊。柳絮覺得自己是眼花了,居然看見文秀娟在發抖。室友們回房的時候,文秀娟正在給自己泡蜂蜜水。這是她為數不多的善待自己的時候,早晚各一杯,雷打不動。
蜂蜜開瓶久了容易粘蓋,所以文秀娟會先在瓶口覆一層保鮮膜,再蓋蓋子。此刻,她擰開蓋子的時候,保鮮膜撕裂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