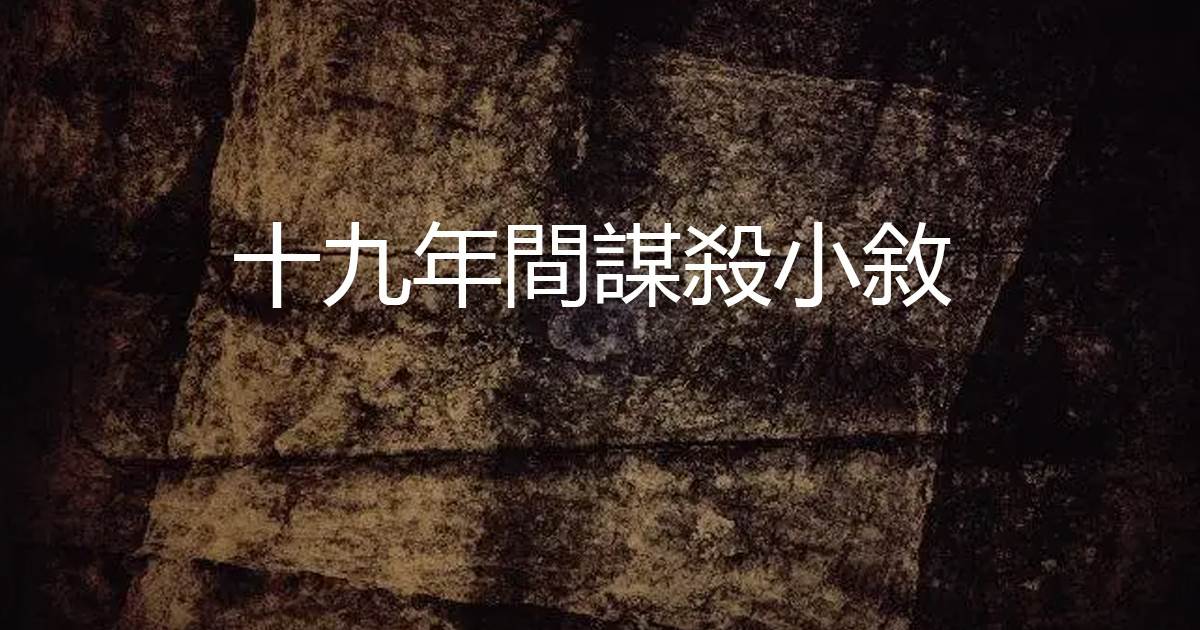《十九年間謀殺小敘》第72章
等兩個人吃完的時候,食堂里已經沒什麼人了,回寢室的路上經過二教,文秀娟想起了自己上周末的請托,應該是今天能有些結果,就找了個借口,讓柳絮幫她把飯盒先帶回去,自己上了二教三樓。
二教是藥學院,毒理實驗室就在三樓。文秀娟走在樓梯間里,覺得身后遠遠的有腳步聲,那腳步聲不緊不慢,還有些熟悉。其實出食堂的時候,她就覺得身后仿佛有人跟著,這種感覺自從知道有人下毒后經常出現,無疑是壓力太大產生的過敏,先前柳絮在身邊,她不想表現出來,就忍住了沒回頭看,可現在這樓道里,難不成還是自己過敏?出了三樓,走了一段路,文秀娟終于還是忍不住回了回頭,看見馬德從樓梯間轉出來。班級里面,馬德不屬于最看不慣她的那撥人,見了面,基本的招呼還會打。但文秀娟此行的目的,并不想讓同學知道,微笑點頭后就沒再多說,徑直走到毒理實驗室門口,馬德卻還跟在后面。文秀娟停下馬德也停下,她只好問,你來這兒?馬德說對啊我在這里做實習生。文秀娟心頭就是一跳。馬德越過她進了門,文秀娟愣了一會兒,看見她的趙龍走出來和她打招呼。
“這兩天太忙啦,做了一部分吧。汞、鉍、錳、鈾、釩都給做了,沒什麼特別的,你那列表上還有三分之二,有些的試劑還真不好找。”
趙龍是藥學院的大三生,拉小提琴,兩個人是在團委搞的音樂演出時認識的,趙龍不知道委培班里文秀娟的流言,對這個漂亮學妹印象相當不錯。
ADVERTISEMENT
所以當文秀娟拿來一小包指甲頭發請他在實驗室里化驗的時候一口答應了。文秀娟當然沒說是自己的頭發,假托一個好朋友要寫論文,是關于都市正常人體內各種輕重金屬含量是否超標的,需要一些數據。需要檢測的金屬種類列了長長的一串,每一種都要對應的試劑才能檢測,其實是頗麻煩了,學長學妹間的幫忙,本不必要做到這種程度,趙龍肯答應,顯然是對文秀娟有所企圖。性命攸關,對這點企圖,文秀娟也就生受著了。
“馬德什麼時候在這里做實習生的?”
“有一陣了,怎麼啦?”
“你讓他幫忙了,幫忙做這個化驗?”
趙龍愣了一下,開始支支吾吾起來。當時是答應了文秀娟親手做的,但有這麼一個好用的實習生,為什麼不讓他去干呢,他沒想到文秀娟還真在意這點。
突然而至的巨大情緒一瞬間把文秀娟整個腦袋都淹沒了,接下去的兩分鐘里她完全不受控制地埋怨乃至怒罵,具體說的什麼她事后已經回想不起來了,只知道趙龍的臉色變白變青,最后扔下一句“真是不可理喻,真是莫名其妙”,就扔下她回了實驗室。
文秀娟漲紅了臉,喘著氣,盯著緊閉的毒理實驗室大門看了很久,后悔慢慢升了起來。馬德雖然不能排除下毒人的嫌疑,但并不是嫌疑較高的那兒個,當然他有可能把自己做這些檢驗的事傳出去,傳到下毒者的耳中,可是事已至此,自已歇斯底里這麼一通發作,根本于事無補,趙龍不會幫她繼續檢驗不說,馬德更是會把這出“軼事”大肆宣揚。
馬德來自農村,也是個要在大城市同學間尋找存在感的人啊。可道理歸道理,情緒歸情緒,該爆發的時候,文秀娟也毫無辦法。她終于明白。自己并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毫不畏懼。自己怕死,怕得要命。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馬德不要說出去嗎?文秀娟抿著嘴唇、轉回身去走向樓梯的時候,看見文紅軍就在幾步之外看著她。
“爸?你怎麼在這兒?”
文紅軍看她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個陌生人。
多少年了,文秀娟從未在人前表現出這副失控的模樣。哦不,這是第二次,蜂蜜那回是第一次。
“沒啥,我就是……想來看看你。”
“食堂那兒你就來了?怎麼不叫我?家里出什麼事了嗎?”
“沒事情。前面麼,你和同學在一塊。”
文紅軍看得文秀娟渾身不自在,然后他說:
“行,我出車去了。你好自為之。”扔下這句話,他轉身消失在樓梯口。
爸爸的這次到訪似乎是突然起意,卻看到了這個僅剩女兒的另一面。文秀娟沒琢磨明白文紅軍到底什麼意思,她也沒工夫把心思放在爸爸身上。她覺得今天有點不順利,回到宿舍,爬上床假作午休,打開了信。
和你一樣。
今天我又干了一次,她完全沒有發現,喝下去了。
過癮。
還沒想出你的辦法?
另一個同學
文秀娟傻在那兒了,在毒理實驗室外被壓制下去的恐懼,加倍地涌來。
這說的是昨天?
怎麼可能,昨天我都喝了些什麼?我有讓水離開視線過嗎?他是怎麼做到的?
文秀娟腦子里一片混亂,一時間回想不起來昨天自己喝過多少次水,每一次是在什麼情況下喝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