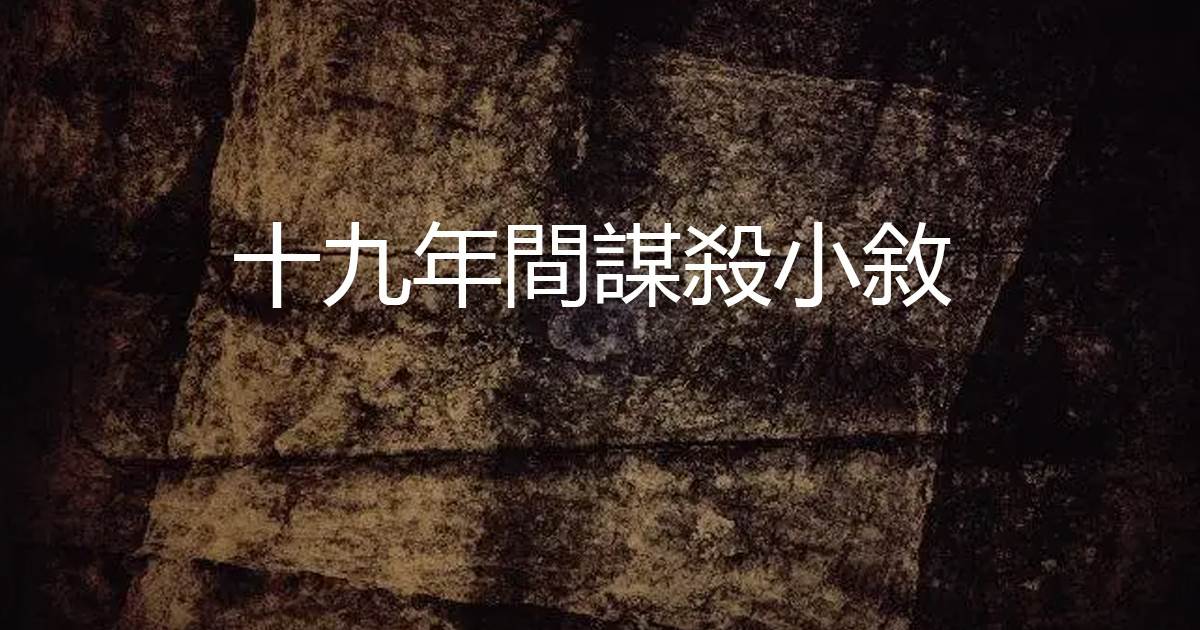《十九年間謀殺小敘》第82章
晚上起來看手術刀,冰冷的刀光滲入骨髓。
丈夫那個時候,到底在想什麼?審視自己的職業生涯嗎?他究竟碰到了什麼過不去的關口?毫無疑問,他心里有事,以至于輾轉難眠,以至于暗夜里凝望,以至于下意識地去做一件無意義的事情。說起來無意義,卻是他內心里某些東西的投射吧。
柳絮的不安已經持續了一周,她本不知道這種深夜里的不安來自何處,但每每總讓她睡得很淺,總是驚醒。如今她知道了,也許半夜起來觀刀是第一次,但夜里枕邊人這麼沉默地注視自己,一定已經很多天了。
他在想什麼?
無來由地,柳絮想到了多年前的那個夜晚,文秀娟半夜里起床,掀起一張張簾子,端詳一張張熟睡臉孔。
黑暗中的凝視,彌散著惡意。
柳絮突地心跳加速。
他是要害我嗎?
他要害我?他要害我!
沒有任何理由,也沒有一點兒證據,只有該死的直覺。
他是在想,要不要殺了自己,他看著自己的脖子,看著那上面的動脈呢!他是要用那些手術刀下手麼,還是在對他救過的一個個人訴說,他是不是想,已經救了那麼多人,殺一個人也抵得過?
這樣的話,原來,文秀娟的死,費志剛是有份的。
郭慨死后,柳絮接過郭慨的調查線索,開始了對這宗九年前謀殺案的調查。她豁出去了一切,當然也就不會像之前那樣刻意瞞著丈夫。她本以為費志剛一定和案子沒有關系,畢竟連文秀娟自己,唯一排除了的兇手,就是費志剛啊。
ADVERTISEMENT
可現在,費志剛想殺自己。
也許只是一個徘徊不去的惡念,也許并不真的會動手,也許是自己在瞎猜誤會了……
柳絮閉起眼睛。
如果是郭慨,他會怎麼判斷?
柳絮記起他在《犯罪學》課本扉頁上寫的一句話:偵查員不應放過任何微小的可能,因為不常見的惡性案件,往往源自不常見的微小可能。
即便費志剛不是謀殺者,他對當年文秀娟之死的介入程度,也一定不淺。
天亮之前,柳絮還是睡著了,醒過來的時候,費志剛已經去上班,拉開窗簾,外面太陽不錯。人總是在夜里會對世界抱以極大的不安和恐懼,白天的時候,就會樂觀許多。
或許自己只是多心,柳絮想。那是一個和自己生活了那麼多年的人啊。
她轉回頭,似乎看見郭慨坐在床頭沖她笑了一笑,又不見了。這是恍恍惚惚間夢幻泡沫上的倒影呵。
他在擔心著自己吧。那麼,小心一些總沒錯。
2
要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相?柳絮覺得,郭慨在手把手地教她。這幾乎不是錯覺。
郭慨的死和文秀娟的死串在了一根繩子上。
為了獲得郭慨最后的幫助,盡管覺得難以面對他的父母,柳絮還是在兩周前敲開了郭家的門。二老都在,一望而知,那是兩具喪失了所有熱力的枯萎的軀干。
“我們家慨慨。”郭母這樣開始念叨,令柳絮恍如回到二十年前,郭慨在弄堂里飛奔時,他母親就是這麼喊他的。她也有好多年沒有見到郭慨的父母,郭慨對她曾經的憧憬當然瞞不過父母,見到柳絮上門,他們也并不特別意外。
或許對他們來說,很想和人多說說兒子,這樣就好似郭慨的痕跡還沒有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無論那個傾聽者是誰。
“他做戶籍警,我們放心一點,哪里想得到他那些做刑警的同學都還沒有出事,他自己先沒了。”
“怎麼可能呢,他多老實的一個孩子,怎麼能晚上去那樣子的酒吧,還和不明不白的女人走了。他不是那樣的人啊,你知道的啊。”
“咳,警察說會全力查,領導也來了家里兩次。日子一天天過去,沒個說法。倒不是說我們做父母怎麼怎麼樣,孩子是看著長大的,什麼秉性我們會不知道?別的不說,這孩子要真是,啊,真是那啥,干什麼還要發個地址到另一個手機上呢,沒有這樣的吧,他肯定是有了什麼懷疑的。你說對不對?”
“我早就和他說了,慨慨,你既然現在已經不是刑警了,就安安心心做一個戶籍警,別再去沾些危險的事情,那些事兒和你現在沒關系了。他就不是個聽勸的人啊。我就覺得他不對勁啊,有事情,他不和我們說。他肯定是專門去查那些人的,那些人太惡了啊。”
柳絮局促地坐在小客廳的沙發上,雙手交疊在膝蓋上。郭父和郭母無法接受兒子的死,更無法接受兒子是受了女人的誘惑而死,他們覺得郭慨一定是知道了這個邪教的事情,獨自調查而遇害的。她只好保持沉默,她該怎麼告訴二老,郭慨是因為她而死的呢?
柳絮問起那部記錄郭慨行程的手機,結果還在警方那里。但似乎手機上的內容并沒有對警方破案提供多少幫助。
柳絮想,多半是因為那個故布疑陣的邪教線索,把警方的偵破方向給帶偏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