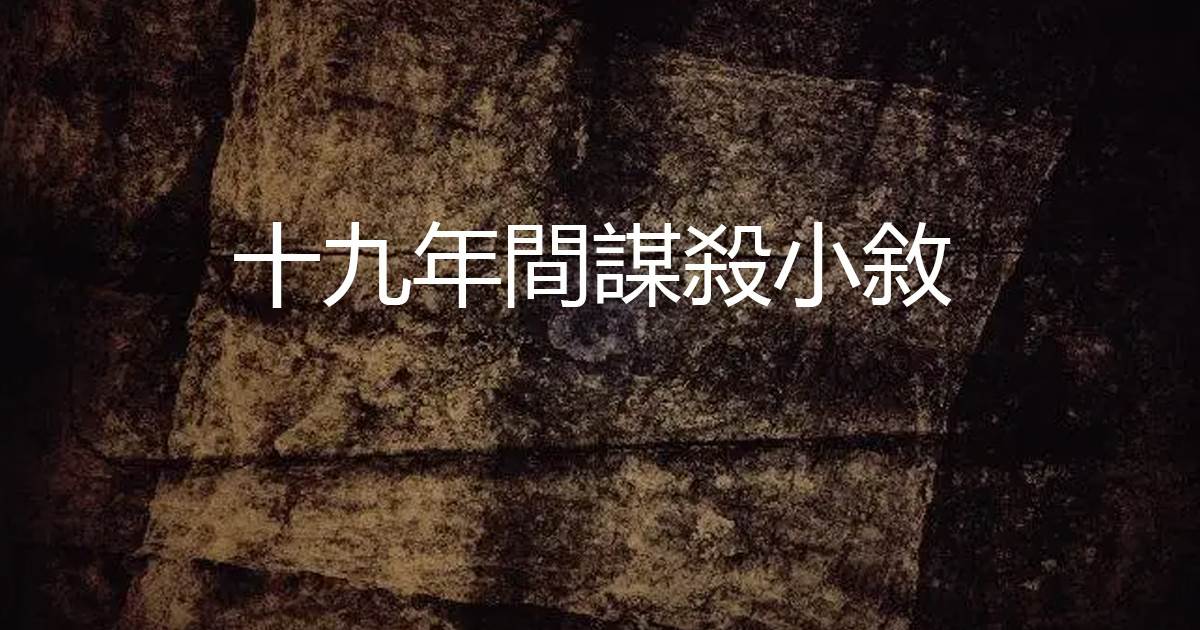《十九年間謀殺小敘》第114章
然后,一塊濕潤的帶著濃烈麻醉藥味道的毛巾蓋在了她的臉上。
失去意識之前,柳絮終于想起了他的名字。
馬德。
4
仿佛有巨象長鳴,那深沉厚重的嗡嗡聲自無名之處而起,震顫著柳絮的骨肉和血液,最后連魂魄都酥麻起來,柳絮的意識隨之回流。
她睜開眼睛的時候,那聲長鳴猶自橫亙著。久久不散。她記起了這小時候常常聽見的聲音,是黃浦江上輪船的汽笛聲。
她躺在一處柔軟的地方,睜眼看到的是有著大攤銹跡的鐵皮屋頂,她想自己是躺在一張沙發上,掙扎著要坐起來,卻發現全身依舊酸軟無力,沒能成功。
“很多年沒見了吧,老同學。”
一個聲音從很近的地方傳來。
事到如今,已經是圖窮匕見之時,這出在幽幽暗暗的舞臺上綿延了許多年的生死劇,就要拉下帷幕。
柳絮心思出奇的鎮定。她正面對著殺害郭慨和文秀娟的兇手,一種特殊的力量此刻牽引著她,使她遠離憤怒或者恐懼這樣平凡的情感,她似乎預感到了終結,仿佛一切都早已經安排好,接下來命運就將展示結局。
柳絮攢了一會兒氣力,把雙腿先從沙發挪到地上,然后手、腳和腰一起使力,讓自己勉強正坐在沙發上。馬德就坐在她對面看著,沒有干涉,讓她保持了體面。
柳絮沒有去瞧馬德,而是打量四周。
放眼看去,柳絮心里驟然一緊。剛才死生無懼的平靜,立刻就被打破了。一重又一重的目光自四面八方而來,讓她有深陷重圍之感。
ADVERTISEMENT
柳絮定了定神,意識到這種壓迫感只是來自無生命的雕像而已。在她的周圍,在這間一眼望去三四十平方米的鐵皮屋子里,擺放著數十尊形形色色的雕像。這些雕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還有象、牛、馬等動物,都不知在風雨中矗立了多少年,不僅斑駁,而且多有缺損。然而這歷經了時光的斑駁和缺損,每一片每一段,都像為它們點燃了靈魂之火,令它們不言不動,卻凜凜然蘊了股神氣。而今它們匯集在這間小屋子里,高低錯落地擺放著,仰面俯首向各方,似在無形無影間切切密密地交流著什麼。
屋里的其他陳設極簡單,一張方桌幾把椅子加上柳絮躺著的沙發而已,側身于這些雕像之間,變得毫無存在感。靠柳絮右側有一排大窗,窗外空茫花一片,便是黃浦江了,現下天色未晚,可以看見對岸浦東的幢幢高樓。
“我這是在哪兒?”柳絮問。
這就是柳絮的第一句話。她沒有問你為什麼抓我,你抓了我要干什麼,也沒有怒斥馬德是個冷血的兇手。就像馬德說的第一句話一樣,平凡而普通。
“一座孤島,”馬德說,“這里大概是市區最后一片廢舊堆場了。其實已經廢棄不用,地還荒著沒清理。可惜我們開車進來的時候你沒能看見,這景色是有點壯觀的,幾層樓高的鋼鐵垃圾,還有廢棄的車殼子,一座立體的墳慕,迷宮似的,車小蟲子一樣彎彎繞繞地開。開到最里面就豁然開朗,臨著江邊一大片的空地,空地里一個二層高的天臺,我們就在天臺上的鐵皮屋里,有那麼點世外桃源的意思。”
馬德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另一邊墻上的窗前,窗臺上放著一個小小的孩童頭像,原本應該是個全身像,脖子往下已經不見了,只留個小腦袋對著窗外,頗有些詭異。馬德手搭在孩童腦袋上,向外張望。
“這里看出去的景色,你在其他地方見識不到。往你這一邊看,黃浦江上輪船如過江之鯽,對岸高樓鱗次櫛比,如果到了晚上,一片燈火輝煌間還閃著各種霓虹廣告,終夜不息。黃浦江是上海的生命河,你可以見到這座城市的生長和活力。”馬德說著他背后的景色,仿佛正目睹。
“但是站在我這里看出去,是一片又一片巨大的廢棄物堆成的廢城,是科幻片里世界末日后的城市模樣,好似這座城市已經死去多時了。而我們所處的這間屋子,就在生與死之間。這是看堆場的老頭子一手弄起來的,他在這里一住幾十年,也是個奇人。”
馬德輕拍著孩童的頭,說:“這些都是他從下面的廢舊破爛里淘出來的,一個人住孤單吧。外面的平臺上也有,下面靠平臺的空地上也有,像個石人陣似的,是不是感覺有點可怕?他幾個月前得病死了,現在知道這座城市里有這麼一處隱秘的廢城桃源的,也沒幾個人了,有一天這里開發了,一切全都被清理掉,也就再也不存在了。最近這兩三個月,我常常會來這里,一待就到深夜。我發現和這些雕像在一起,反而是會格外孤獨的,你覺得和他們在交流,其實卻又沒有。這種反差。
再看看兩邊截然不同的景象,你會有種遺世獨立的清醒,更能看清楚自己,看清楚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系。”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