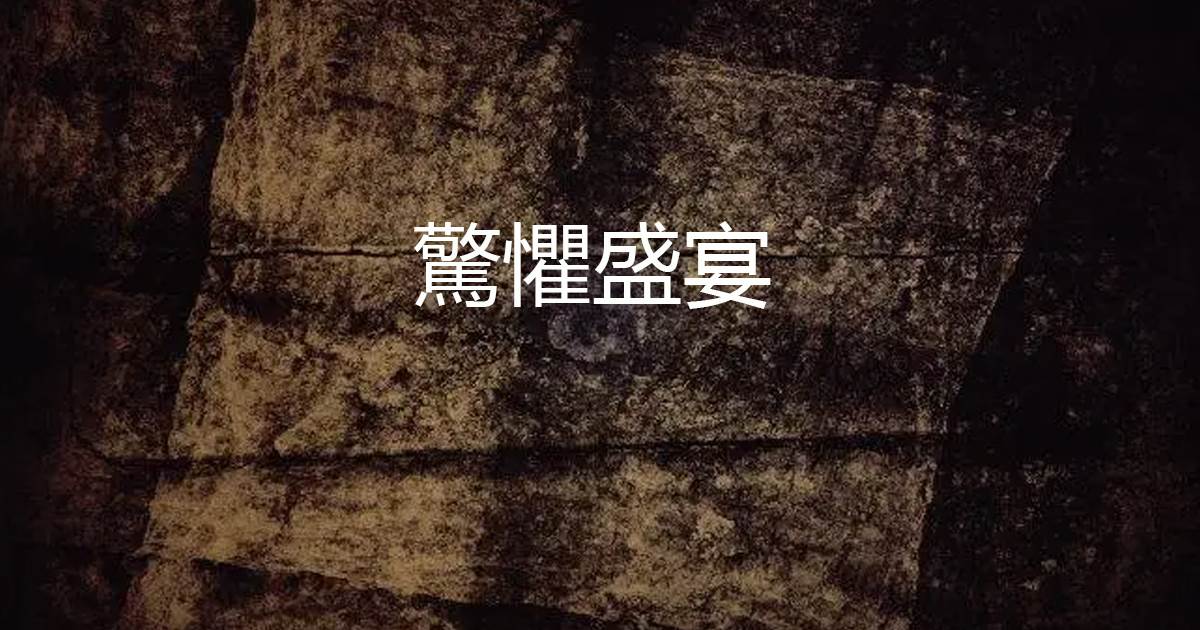《驚懼盛宴》第388章
“師從禮,我們相識……有二十幾年了吧?”
秦也問道。
“二十二年,老板。”
被他稱為師從禮的中年男人低沉地回應道。
“那你回答我……我在做的事,對嗎?”
過往的二十年間,多少次有人告誡他,錯了!
有好言規勸,有出言相譏,有同情憐憫,有怒目而視——
秦也總是那麼堅定,他編織了一個美夢,并把森羅面相的每個人都拖入了這個夢中,除了……師從禮。
二十年前那次劇變之后,還站在他身邊的同伴,只剩師從禮了。
也只有師從禮知道,秦也到底在做一件怎樣的事。
“追求更長久的生命,是生物的本能。”師從禮平靜地說道。
他看著已經浮上海面的朝陽,沒有去看秦也。
秦也的意志早已經堅定,現在秦也的話與其說是迷茫,不如說……是他在對過去的自己做最后的道別。
師從禮不知道秦也這一趟去東京都后發生了什麼,他只知道,自己只要一直站在他的身后,就足夠了。
時間,生命……
森羅面相的成員都為了同一個目標而來。
他們的來歷各不相同,背景中也摻雜著各個勢力。
但秦也不在意,師從禮也不在意。
正如師從禮說的那樣,追求更長久的生命是生物的本能。
世上絕大多數人在時間的壓力之下,忙著把生活穩定,工作、家庭、子女。
在什麼樣年齡,按部就班地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至于夢想?
人們更喜歡聽成功人士去分享自己為了夢想拼搏的故事。
畢竟,大多數家庭是沒有試錯成本的。
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為了夢想,到了三十歲還一無所有,四十歲仍然顛沛流離,五十歲身邊空空如也,六十歲俯仰孤身一人時,是會后悔的。
ADVERTISEMENT
師從禮本也那樣認為。
他出生自書香門第,在遇到秦也之前,他的想法甚至更加保守。
可秦也告訴他,除了長度之外,生命還有寬度。
生固然重要,但落腳之處,在命。
只求生不為命,就算活得再久,也不過是一場循規蹈矩的重復。
一只在夏季縱聲高歌,肆意飛行的蟬,和一只深陷泥潭,不動不走的龜,一個只活一個精彩的夏季,一個卻能存在數十個春秋,甚至更久,但它們的生命誰更精彩,卻沒有人知道。
人類也是。
自古便有匆匆百年的說法。
絕大多數人的壽命甚至根本達不到百年,但在這匆匆而過的人生中,卻可以憑借學習,感悟,體驗,踐行等行為,將之無限拓寬。
“你想做一塊石頭,還是做一只精衛?”
二十年前,秦也這樣對師從禮問道。
師從禮沒有思考多久,很快就做出了回答。
也是從那一刻起,師從禮才明白秦也真正要做的事。
人活過,便有痕跡。越是活得掙扎的人,痕跡便越深。
這些年,秦也一直在掙扎。
彷徨、焦慮、恐懼、崩潰……人類的本能和他后天的意志不斷對抗,沒有人知道他背負著什麼,要做些什麼。
就連師從禮,也不完全知道。
但他愿意相信,那個告訴他生命如何呈現要憑自己決定的人,是不會屈服于時間的蠱惑的。
就算不與那些鬼物為伍,秦也也能依靠自己,帶著猙獰的掙扎痕跡躍入沒有時間限制的歷史長河之中永存。
“我見到文玉了。”秦也忽然笑了起來,“那小子,以為自己是另一個人呢。”
“你沒告訴他當年發生的事?”師從禮問道。
“沒有。”秦也搖頭,“他本就不該牽扯到這些事中。”
“如果不是羽生七穗那個女人……文玉會在家鄉安穩地過完一生。”
秦也捏緊了拳頭,晨風自海面上吹來,帶著一股涼意吹得他的衣襟獵獵作響。
“她躲在平安時代已經二十年。”
“我會讓她知道,她是錯的。”
秦也松開了捏緊的手,微微閉上了眼睛:“我們選擇了精衛,但更多的人選擇了亙古長存的石頭。”
秦也扭過頭,看著師從禮:“從禮,你做好與他們為敵的打算了嗎?”
師從禮微微欠身,笑道:“二十年前就已經做好了,老板。”
————
當秦文玉背著水原涼子,帶著伊吹有弦來到阿忙的實驗室時,阿忙正靠著墻發呆。
倒是松永琴子,見秦文玉出現后表現得有些激動。
她實在受不了阿忙的古怪行為,一個人莫名其妙的大哭大笑,大吵大鬧,他時而平靜如水,時而又歇斯底里的瘋狂。
相比之下,還是秦文玉要好上一些。
“你欠我一個解釋。”秦文玉把水原涼子交給伊吹有弦照顧后,徑直走到了阿忙身前。
阿忙微微抬頭,渙散的瞳孔逐漸凝聚,咧嘴笑道:“是你啊。”
“你從我身體里分離出來的到底是什麼?”秦文玉問道。
阿忙一怔,目光朝四周找了一下,落在了伊吹有弦身上,說道:“你知道了?”
沒等秦文玉回答,他便繼續說道:“對,你沒有兩個靈魂,也沒有兩個意識,你只是有輕微的自閉癥狀。”
“至于,從你身體里取出來的是什麼東西,我無法告訴你,你可以去問你的父親秦也,或者你的母親……”
“至今還留在平安時代的——羽生七穗。”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