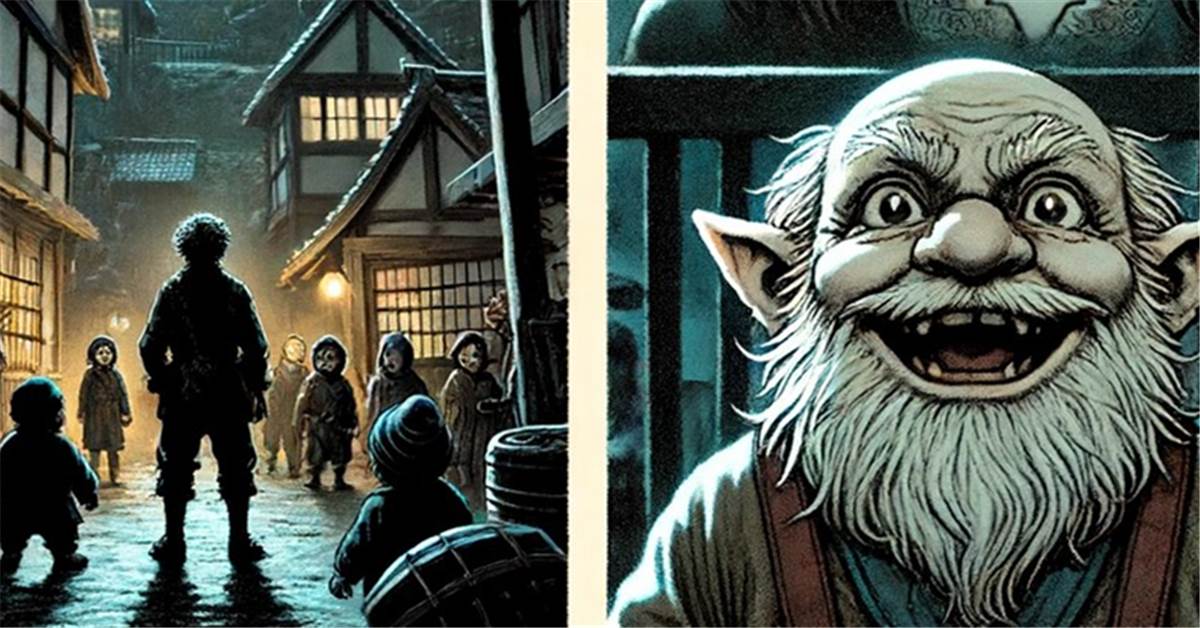《增高村》第21章
「你們曾高村,被邪靈詛咒了。」我采用了煽動性的說法。
「它,挑中了我的這三個孩子。」
我語氣沉重:「想要阻止光圈縮進,就得作出獻祭,不然大家都得死。」
「怎麼會這樣?」他倒抽了一口涼氣。
「我,下不了手。」我說,「只能求其他人了。」
他向我再三確認:
「劉哥,一定要這麼做?就沒其他辦法了嗎?他們可是你的……」
我「嗯」了一聲,斬釘截鐵。
電話那頭,沉默了半晌。
「好,我幫你。」他同意了。
我告訴他一個地址,那三個孩子,現在在一間空別墅里。
為了不讓婉秋阻止這件事,昨晚,我一個一個地把他們搬走了。
還好他們是定格的,給我的感覺,像在搬童裝店的塑膠模特,假人。
現在,他們估計在那里哭,喊媽媽?喊爸爸?
我甩去了這個念頭,跟曾開朗囑咐道:
「客廳的柜子里有安眠藥,不要讓他們痛苦,留全的。」
「完成之后,給我拍段視頻過來。」我補了一句。
「明白了,劉哥。」
我上車,讓司機載我去醫院。
路上,我突然收到部下的緊急消息,說瞞不住了,全城失控了。
一傳十,十傳百。
所有人都知道了,有個致命的光圈,在越縮越小。
下一秒,我看到了烏泱泱的、神情恐慌的人群。
在路口,像閘口泄洪一樣,震天動地,摧毀了所有的路障,直沖市中心而來。
我嚇得魂都沒了。
「掉頭!掉頭!」
31
還好,栗旬大廈就在距離我不到五百米的距離。
頂層有我的私人直升機。
我立馬換交通工具,飛去了醫院。
在天臺一落地,直奔手術臺。
主刀醫生和十幾名醫護人員已經恭迎我已久了。
外面都亂了套了,能看出來,他們神色稍微有點緊張,但依舊保持專業。
ADVERTISEMENT
醫生讓我先量身高,接著量大腿,在我的大腿根部,精確地畫好切割線。
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我的訴求:
我術后的身高,必須從 1 米 86「掉」到 1 米 26。
也就是,截去我半米多的大腿。
我特意囑咐主刀醫生,跟提醒賣切糕的販子似的:
「不夠可以再切,你別給我切多嘍。」
「這你放心,劉總。」醫生似乎被我逗笑了,「您準備好了的話,我現在給您上麻藥。」
我摸了摸我那雙大長腿,腦海里浮現我當侏儒這些年的畫面。
我在腿上面捶了幾拳,讓自己不要留戀。
等等,怎麼有臺電鋸在手術臺旁邊?
臥槽……真把我嚇到了。
醫生說,截肢就是要用電鋸的。
這我還真不知道……
望著那把電鋸,我突然感到心慌喘不上氣,像蹦極要往下跳似的。
「沒事的,很快就過去了。」醫生安慰我說。
我說:「你先把它移開……不要讓我看到。」
過了一會兒,醫生再次詢問我:
「劉總,準備好了嗎?」
這時,我接到了婉秋的電話。
「老公,外面什麼情況?!孩子去哪兒了?!是不是在你那兒?」
這時,曾開朗也正好給我發來了一則消息和一則視頻。
他說,事辦妥了。
我對醫生說:「先等等……」
我找了個空房間,做了好幾個深呼吸。
我打算,先狠心切割掉我和婉秋的這段關系,增加勇氣,再進行截肢手術。
婉秋喊道:「你說話啊!急死個人了!」
「我再次強調,我不是你老公。」我說,「還有,那三個孩子也不是我的。」
她愣了三四秒,說:「你什麼意思?」
「我什麼意思?賤女人,你他媽給我戴綠帽,生了三個不帶我基因的野種,你又是什麼意思?!」
我真希望,在我說這段無理取鬧、極度難聽、足夠摧毀夫妻感情的話,她會沖我發狂,徹底和我翻臉。
這樣我就不用發那段視頻了。
她說:「哈,哪家機構的基因檢測報告?我和你再去十家,有一家檢測不出來算我輸,到時候別打臉哦。」
在我前面的種種操作之后,她好像對這種話免疫了,我表現得多渣,她都覺得我在演戲。
我十分艱難地擠出一聲冷笑:「晚了,我已經送他們去投胎了。」
我把那段視頻發了過去。
婉秋說:「呵呵,我不信,你會對自己的孩子下毒手。」
沉默。
沉默。
電話那頭,突然爆發她歇斯底里的尖叫。
「你把他們怎麼了?!」
「柏瀚,你快醒醒!小桃子和小星星不會游泳,快去救你妹和你弟……」
「姓劉的!你快去救他們,我求你了……快去啊嗚嗚嗚……」
我不小心,也點開了那段視頻:
只見,這仨小孩在水里,像睡著了一樣,并排地沉在游泳池的池底。
面容蒼白,了無生氣。
我嚇了一跳,連忙關了。
小星星的樣子……和我那天晚上在浴室里看到的嬰兒死狀一模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巧,曾開朗偏偏采用了這個方法。
吃大量安眠藥,讓他們溺水。
是湊巧……還是……當初我看到的靈異事件,其實是一個預兆?
預示著,我會有小孩,但會死在水里……
這時,我聽到了不遠處傳來轟隆隆的房屋倒塌聲。
我想起來了……這不就是那天晚上我搭石屋子聽到的怪聲嗎?
大廈倒塌的聲音。
預示著將來這里會興建起很多建筑物,但是會全部倒塌……
我突然感到背脊發涼。
難道說,我之前每天深夜在村里遇到的靈異事件,其實都是在暗示,我后面會遇到的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