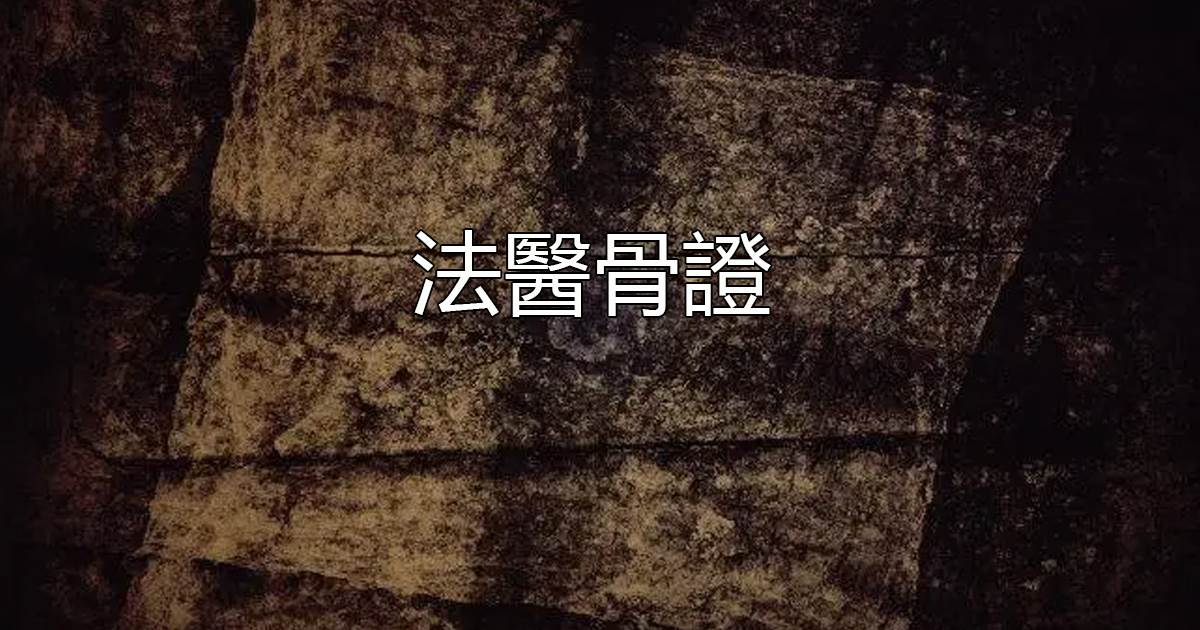《法醫骨證》第2章
可他聽人說起,公安廳的人都不好惹,這兒可是人家的地盤,說什麼也得憋著。
王亞雷想起經常在公安內刊上看到有關蘇天易辦案的報道。
蘇天易原先是江越大學法醫系副教授,兩年前調入公安廳刑警總隊后,成了全省刑警內部人人皆知的法醫骨證專家。
報道只說他辦案如何一絲不茍,又如何通過對骨頭縝密分析,抽絲剝繭,屢破大案,是刑警總隊不可多得的一把尖刀。
從報道中的照片上看起來,蘇天易是個四十來歲沉穩可親的科學家模樣,卻沒料到他說話像是暴躁的獅子座,有點霸道,特別不講理。
“這……這……蘇法醫,因為我們那邊的案子還在繼續勘查現場,法醫忙不過來,所以就……”王亞雷也是實話實說,東嘉縣公安局僅有一名法醫,抽不開身,而他平日里工作吊兒郎當的,大隊長自然就將這種不用動腦筋的苦差事派給他了。
“我見多了,你們總能找出一萬種理由,我不需要你們的理由。
”蘇天易的臉上忽然浮起一副難以形容的傲慢表情,直視著王亞雷,“不過,看骨頭,找我就對了。
”王亞雷見蘇天易雖然冷言冷語,可是并沒有拒絕自己,心里頓然舒緩了許多。
他本來還擔心遭到拒絕,自己完不成大隊長交給的任務。
他定了定神說:“蘇法醫,那就麻煩你了。
是這樣的,昨天我們東嘉下了一場暴雨,大水沖毀了一片山坡,一個小孩在滑坡底下發現了這塊骨頭……”“跟我來吧。
”沒等王亞雷說完,蘇天易便打斷了他,抬起右腿跨上山地車,速速地朝前騎去。
ADVERTISEMENT
王亞雷將骨頭又塞進手提包,拉上拉鏈,右手又習慣性地抹了把臉上的汗珠,跟在山地車后一路小跑。
刑警總隊在三號樓,蘇天易將山地車停放在樓邊上的自行車棚里,招呼此時已經氣喘吁吁的王亞雷走進了大樓。
王亞雷三年前從宋都警校畢業,擔任派出所所長的父親將他硬塞進刑警隊鍛煉。
他心里是一萬個不愿意,當初上警校就是父親逼的,別說畢業了進刑警隊。
他平時貪吃愛睡懶覺,刑警隊的快節奏適應不了,而且很難出成績。
三年來,光是遲到的問題,被大隊長不知罵了多少次。
這是他第一次到公安廳出差,連夜開車過來,一路沒合上一眼,此時一直犯困著。
進了電梯,蘇天易摁了十樓的按鈕,一聲不吭。
他背對著王亞雷,眼睛直勾勾地盯著電梯上端顯示屏上不斷變大的樓層數字,腦海里想著的卻是剛才那塊髖骨。
因為剛才遭到搶白,王亞雷現在輕易不敢說話,怕引起蘇天易不爽,耽誤了大事。
他只想辦成大隊長交給他的任務,要是蘇天易說這骨頭是從荒墳野冢里被大水沖出來的,他立馬就去賓館開個房間睡大覺。
王亞雷的眼睛不經意間瞟到電梯右側壁上掛著一塊樓層指示牌,從二樓到十二樓,刑警總隊各要害部門一覽無余:重案偵查科,冷案與系列案件調查中心,全省指紋中心……十樓是法醫骨證科,十一樓是法醫科。
王亞雷沒想到法醫骨證單獨成了科,忍不住問道:“蘇法醫,原來你們法醫骨證科實力這麼雄厚,還和法醫科分家呀?”蘇天易沒轉身,只是淡淡地說:“法醫骨證科是我來總隊之后單獨成立的科。
金總隊長的意思是,法醫骨證要好好搞,可以和法醫科齊驅并駕。
實際上,法醫骨證科在我們內部被叫做法醫二科,只不過干的活重點側重在骨頭上。
”王亞雷好奇地問道:“那法醫骨證科有多少人呀?”這時候電梯“叮”的一聲,十樓到了。
蘇天易轉過頭來說:“就我一人,我是科長。
”電梯門緩緩地開了,王亞雷驚訝地發現,電梯間正面墻上掛著一塊長方形的黑色大理石牌匾,從上到下陰刻著五個大字:法醫骨證科,他怎麼看都覺得那像極了一塊墓碑。
“先跟我去實驗室吧。
”蘇天易說完,在電梯左側的一扇玻璃門邊的密碼盤上輸入幾個密碼,電動玻璃門便往一邊開去。
王亞雷心里有點緊張,戰戰兢兢地跟著蘇天易走進實驗室。
他發現里面有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的兩側都是裝飾著玻璃墻的房間,看上去至少有十幾間。
迎面的一個大房間著實讓王亞雷大吃一驚,透過玻璃墻可以清晰地看見,那房間少說也有百來平方。
貼著墻壁周圍擺放著許多不銹鋼架,架子上盡是些骨頭。
有被砍過的,有被燒灼成烏黑殘缺的,有畸形怪樣的……除了那些齜牙咧嘴的顱骨之外,他無法分辨那些骨頭到底叫什麼名字。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七七八八的骨頭,突然一下子在眼前冒出。
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這房間的中心位置居然有座平地而起的墳墓。
墳墓下方有個水泥底座,墓體是半橢圓的黃土結構,上面長滿了枯黃的野草,而墓碑已經被移到了墓邊上,黑洞洞的墓穴里露出一口掉了漆的紅棕色棺材。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