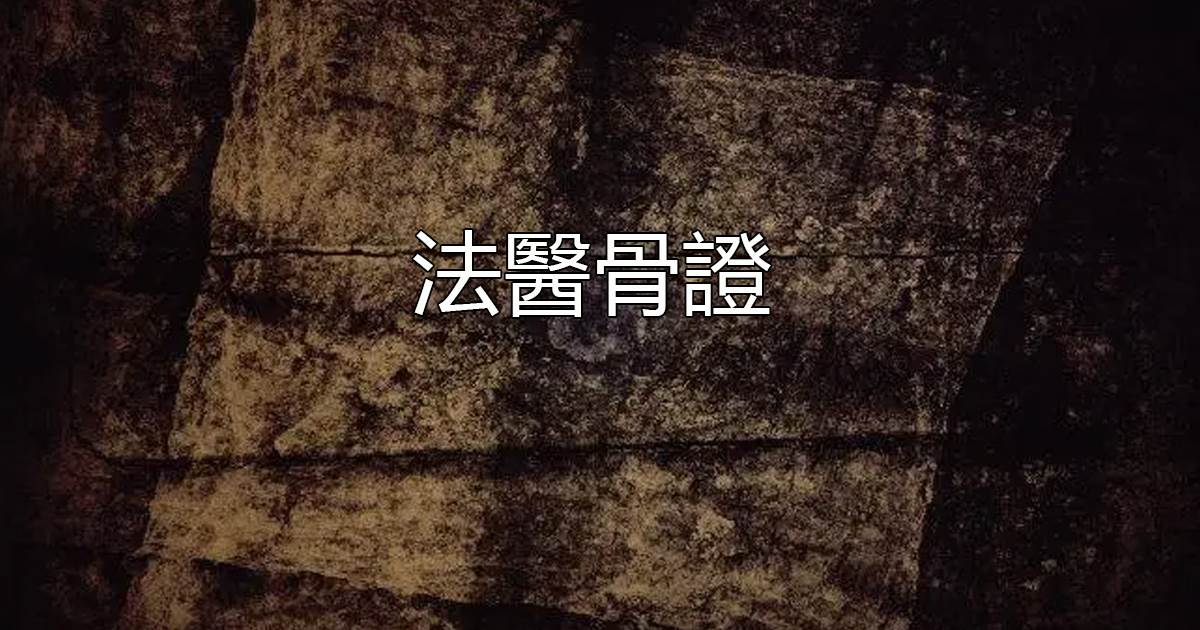《法醫骨證》第5章
”苗小雨說話的時候一臉的認真勁兒。
蘇天易爬下車,站在苗小雨的面前,聳聳肩說:“是五年,死者是五年前死的,骨質還很致密,掩埋并沒有對它造成大的破壞,而且……”“你說是五年?”“是,要是十年的話,骨頭就聞不到腐敗氣味了。
”“而且什麼?”蘇天易接上說:“而且那個破損其實是工具痕跡,如果用放大鏡仔細看,就可以看見鋸子鋸切時留下的鋸痕,你用過放大鏡嗎?”苗小雨漲紅了臉,支支吾吾地說:“這麼大的骨頭,哪里需要放大鏡呀?我……我覺得這根本就不是案子。
你沒去過現場,可能不太了解那兒的情況,那兒原本就有一些墓地,大水沖毀墓地,沖出一兩塊骨頭,再正常不過了。
”“不需要去現場,我只看骨頭就夠了。
”王亞雷停好車回來,發現苗小雨和蘇天易倆在院子里吵個不休,便用責怪的語氣道:“劉大在辦公室里等不及了吧?小雨,看你還不盡快帶蘇法醫去見劉大。
”苗小雨欲言又止,三人走到旁邊一幢小樓底下,沿著樓梯爬上樓去。
劉大的辦公室在二樓西頭,王亞雷推門進去,發現劉大正挺著肥大的啤酒肚獨自坐在茶幾邊抽煙,一張灰暗的方臉上布滿皺紋,仿佛一下子老去了十歲,根本就不像四十多歲的男人。
王亞雷說:“劉大,我把蘇法醫接過來了。
”“哦!”劉大抬眼看了看,激動地站起身來,指指身邊的木沙發說,“坐坐坐,蘇法醫,終于把你盼來了。
”坐定后,互相寒暄了一陣,劉大直切正題:“蘇法醫,你說這是分尸案,依據確鑿麼?”苗小雨歪著頭,挑釁地望著蘇天易,等他說話。
ADVERTISEMENT
蘇天易干咳了一聲說:“劉大,我剛才和小雨法醫探討過了,骨頭上有鋸痕,顯然是個分尸案。
”苗小雨不容分地反駁道:“可我并沒有同意你的看法呀。
”蘇天易也毫不讓步:“你不同意當然可以,可這骨頭的事兒,我說了算。
”王亞雷聽得出來,蘇天易說這話時明顯壓制著怒氣,一定是考慮到了劉大的面子,要是在公安廳,估計他什麼難聽的話都說出來了,他實在為苗小雨捏了把汗。
“可……我們得尊重事實。
”苗小雨還不肯放棄。
“你以為的事實,并不是真相。
”蘇天易冷諷道。
劉大深深地吸了口煙,然后將煙頭掐滅在煙灰缸里說:“小雨,你資歷淺,要跟蘇法醫好好學,我相信蘇法醫看骨頭是有底氣的。
只不過,蘇法醫,我跟你說,我們今天把近十年的失蹤人口檔案都調出來看了,并沒有發現22歲左右的女孩失蹤。
”“那麼前幾年,那個村子里有22歲左右的女孩死亡嗎?”蘇天易反問道。
“倒也沒有。
”劉大搖頭說。
“可能是外地來的流動人口,也可能是兇手殺人之后遠距離拋尸,骨頭是必須要挖的,只有找到更多的骨頭,我們的頭緒才會清晰起來。
”“當然,當然,蘇法醫考慮得比較周全,其實我們也做好了準備,等你一來,我們就動手。
”苗小雨卻插話說:“明天挖起的骨頭肯定會更多,其它骨頭上到底有沒有鋸痕,一看就明白了。
可要是挖出幾塊棺材板,那就不用爭論了,顯然是正常土葬的尸體。
”王亞雷見苗小雨的小圓臉上一陣緋紅,顯然還是有點不服氣。
接下來,劉大將第二天去發掘現場的基本流程跟蘇天易對了對,然后在附近的一家土菜餐廳安排了晚餐。
王亞雷沒想到的是,在餐廳包廂里,苗小雨仍然死揪著蘇天易不放,還將那塊髖骨拿到了餐桌上,拿著放大鏡左瞧右瞧,質疑蘇天易說起的那鋸痕。
蘇天易時而跟苗小雨細心解釋,時而憤然起身踱步。
要不是劉大出面調停,估計那餐桌早已變身實驗臺。
到了最后,蘇天易似乎有點被逼急了,他站起來沉著臉說:“小雨,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想到那場景,連我自己心里都有點發毛。
”王亞雷看到劉大臉上一掠而過的憂慮,但蘇天易終究沒有說出他的新想法,只是說:“我需要更多的依據,現在還不能說。
”兩人吵了一個多小時才開始上菜,吃飯的時候苗小雨還想找蘇天易理論,可是蘇天易全然不顧,只跟劉大閑聊東嘉這幾年來的治安形勢。
吃好飯,王亞雷開車將蘇天易送去東嘉賓館休息,苗小雨也陪著一塊,將蘇天易的行李、山地車搬進房間,那些工作上需要用的箱子仍然留在車上。
回刑警大隊的路上,王亞雷對苗小雨說:“你真是死心眼呀,這個蘇法醫我們是惹不起的,既高傲又古怪。
人家是省公安廳來的,手上肯定有那麼兩把刷子。
我聽說明天晚上張局長要請他吃飯,我們怎麼敢去得罪?”苗小雨卻不屑地說:“那又怎麼了,他厲害我認,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還不讓說了?工作上的事情,誰一時說得清對錯?”王亞雷伸手重重地拍打了苗小雨的肩說:“說你嫩你不信,不要說我沒提醒你呀,小娃娃。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