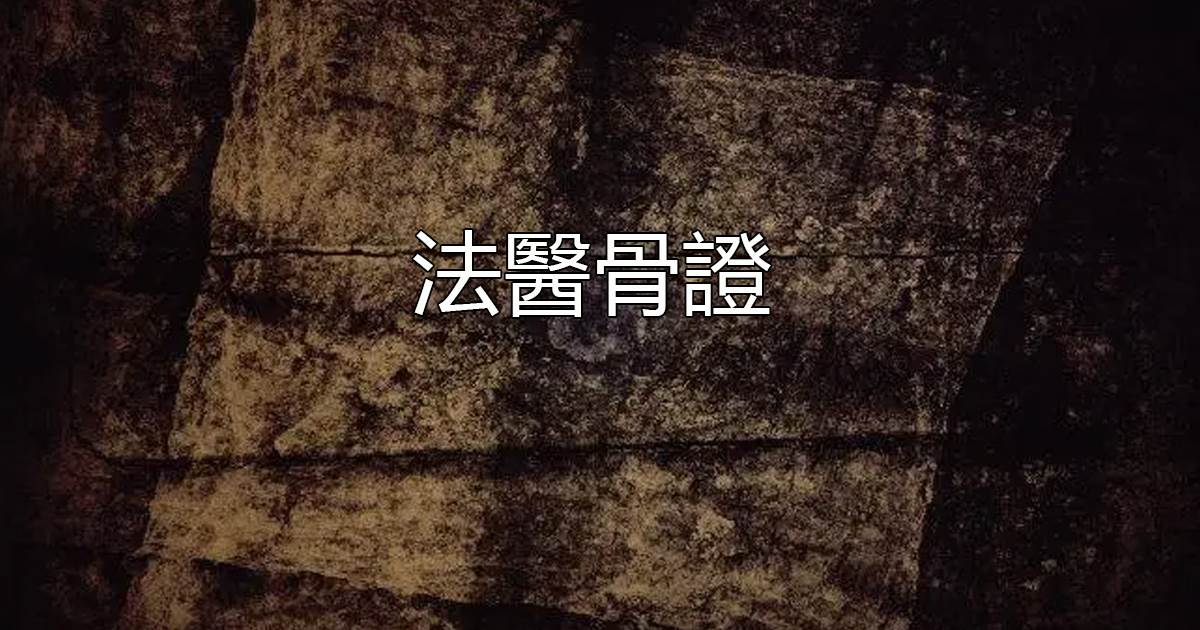《法醫骨證》第26章
東嘉是座小城,能夠嗨到午夜的酒吧只有縣城中心金三角的“醉樂吧”,這間酒吧魚龍混雜,經常發生酒后打斗事件。
王亞雷記得上警校時,有一年暑假在家就聽說那兒捅死過人,他爸爸參加過那案子的外圍訪問工作。
王亞雷心想,要是找到扁頭,或許能夠拿到一些二狗子的情況,于是便騎了自家的摩托車徑直往那兒奔去。
到了醉樂吧附近,王亞雷將摩托車停在對面的一處街角,然后整了整嶄新的紅色印花恤,戴上一副墨鏡,搖頭晃腦地走進酒吧。
酒吧里有些燥熱,燈光昏暗,幾條霓虹燈管在天花板上閃爍著緋紅的光彩。
因為工作的需要,王亞雷的長頭發是劉大默許的,在酒吧這種場合,把長頭發弄亂一點,反而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此時客人已經聊聊無幾,王亞雷橫掃了一圈,見左前方一個卡座里坐著一男一女,兩個人正在玩骰子。
那男的大約二十來歲,染黃發,額頭狹窄,腦袋扁扁的,好像被什麼擠壓過似的。
他左手拿著一瓶開過的啤酒,正對著嘴巴一陣狂飲。
女的穿著暴露,打扮艷麗,右手夾著一支煙,正在專注地看骰子。
王亞雷知道這男的便是扁頭了,于是走了過去坐在卡座對面,說道:“警察,有事找你聊聊。
”“找死就趕緊閃,不要等爺動手。
”扁頭將那女的手中香煙抓過去吸了一口,醉醺醺地頭也不抬。
那女的看到王亞雷,此時卻是慌了,推推扁頭說:“是警察,他說他是警察,你犯什麼事了?”“警……警察?”扁頭抬眼斜視著王亞雷,“我犯……犯什麼事,當然只有警察知道了。
ADVERTISEMENT
”話音剛落,扁頭忽地揮起手中的啤酒瓶就朝王亞雷頭上砸下,王亞雷沒想到扁頭膽子這麼大,想躲避已經來不及了,卡座的靠背頂住了他,只好伸出手臂去抵擋。
“嘩啦!”啤酒瓶被王亞雷的手臂撞得粉碎,王亞雷裸露的手臂上被劃開了一道口子,鮮血頓時冒了出來,溶化在白花花的啤酒泡沫里。
扁頭一擊未中,貓腰拔腿就逃。
王亞雷從卡座上飛奔而起,直追扁頭。
扁頭跑過吧臺時,伸手將臺面上一排大大小小的酒瓶一掃而落,那些瓶子在地上被摔得粉碎,酒香撲鼻,一地碎玻璃,擋在了王亞雷面前。
王亞雷縱身跳過碎玻璃,直撲扁頭。
扁頭沒命地沖出酒吧,往西街狂奔而去。
王亞雷見自己的摩托車正好停在西街角,急忙跨上摩托車,朝扁頭追去。
大街上街燈昏暗,已經沒有了行人,王亞雷猛轉油門,摩托車嘶吼著朝前沖去,不一會兒就追上了扁頭,扁頭已經氣喘吁吁。
“繞過我吧,警察同志。
”扁頭停下腳步,蹲在地上喘氣。
王亞雷停住車,掏出一副手銬將扁頭銬了起來。
扁頭喊道:“我沒做什麼壞事呀,你銬我干嘛?”王亞雷伸出右手臂喊道:“光襲警這一條,就可以讓你蹲進去!”王亞雷將扁頭帶到刑警隊自己的辦公室,先給他來了一套標準的思想教育,然后才轉到了正題,問他二狗子現在哪里。
扁頭大笑道:“警察同志,你不早說,原來你是要問他呀?我告訴你,二狗子早就死了。
”王亞雷心里一涼,面上裝著鎮定的樣子,問道:“你親眼看到的?”“不是死了,還能咋地?五年不見了,也沒聽說過他曾在哪里冒過泡。
”王亞雷唬道:“你跟他做的那些事,我們這兒都摸清楚了。
”扁頭一聽,慌了,支支吾吾地說:“我……我沒做什麼事呀,以前我跟他混,都是聽他安排,可是后來他不要我了。
”“你老實交代,他安排你做什麼了?”“就……就那種事。
”“什麼事我們知道,要不要坦白,那就看你的態度了。
”“二狗子叫我帶女人到他家,讓他拍照,裸的那種。
他把照片拿去賣,賺了很多錢。
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那些女的自己愿意的。
”“你帶了誰去?”“事情都五年了,我哪里還記得?再說,那些女的,都是酒吧里做的,沒一個正經,誰知道她們是誰呀?”“帶過幾個?”“也沒幾個,我記得帶過兩個給他。
”“名字呢?”“不知道。
”“那小名呢?”扁頭搔搔頭,想了半天說:“好像有一個叫阿雪,另一個實在記不得了。
”王亞雷心里一怔,因為他記得蘇天易跟他提起過,說是有個女記者在找失蹤的妹妹,妹妹叫張文雪,這“阿雪”到底是有個“雪”字,或許也只是巧合。
“還記得阿雪的樣子嗎?”王亞雷問。
“真的記不清了,我只記得她瘦瘦的,個子不是很高,下巴有個美人痣。
”“那你后來有沒有見過那兩個女人?”“想不起來了,這些女人成天跑來跑去的,拍完照拿了錢,說不定就去了別的城市,見不到很正常的。
”王亞雷又問道:“另外一個女孩長什麼模樣?”“另外一個胖一點,對,阿雪先去的,后來帶了胖的那個過去,只記得這麼多了。
”王亞雷見問不出新東西,便換了個方向:“那你們把照片賣給了誰?”“不是我們,是二狗子他。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