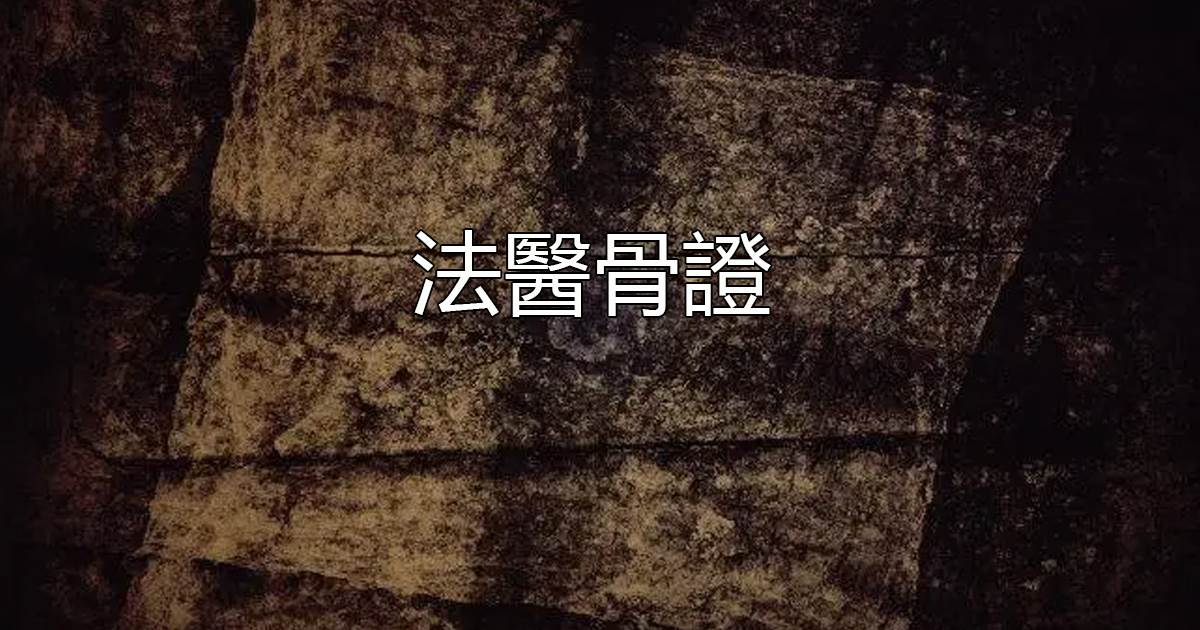《法醫骨證》第34章
咱們該開車的開車,該搬骨頭的搬骨頭。
”苗小雨低頭,吹開杯中漂浮著的菊花花瓣,微啜了一口,又隨手從包里掏出一個筆記本擺在桌上,說道:“有蘇法醫沒錯,可我也不能給他丟臉呀。
”蘇天易撅了下嘴巴,仰頭說:“把工作做扎實了,其它的不要想多了。
”王亞雷一路上都在想,蘇天易說讓他加入法醫骨證科是金總隊長的意思,他就有點不明白了。
雖說在東嘉刑警大隊干了三年偵查工作,可他自己知道,這三年差不多就是混過來的,要不是偶爾投機取巧出了點成績,早就被劉大踢出刑警隊了。
一路上蘇天易板著臉不說話,也不敢多問,他感覺現在逮著機會了,不由得問道:“蘇法醫,我……你為什麼看中我呀?”蘇天易冷冷地說:“你偷看了我的工作筆記。
”王亞雷臉上忽冷忽熱的,感覺蘇天易就要暴怒了。
他瞟了一眼苗小雨,見苗小雨正跟他做鬼臉,尷尬地說:“蘇法醫,我那不是故意的,你的工作筆記沒有合上,是我不小心看到的,往后我不敢了。
”蘇天易瞪了王亞雷一眼,繼續說道:“然后你推動了整個案子的發展,我覺得你是塊干刑偵的料,決意讓你加入總隊,名義是借調,期限是一年。
先跟著我干,我這邊大多是現發的命案,打基礎正合適,往后你要是想去總隊搞重案、冷案或者系列案,我可以推薦你過去。
”王亞雷一聽正中下懷,可他覺得幸福來得太快,心里有點不自信了,說道:“蘇法醫,我實話實說呀,我只是東嘉的小民警,你這法醫骨證科的活,我完全不懂呀。
ADVERTISEMENT
”蘇天易說:“不會讓你干法醫的活,法醫的活有小雨幫我,我會讓你參與到調查訪問里頭去。
記住,你跟我出來,那是代表省廳刑警總隊的,忘了東嘉的身份吧,好好干。
小雨,你也一樣。
”苗小雨說:“我會努力的。
”王亞雷心有余悸地說:“我試試。
”蘇天易說:“沒問題的,我不會看錯人,你們現在是我的左右手。
我們的目標是,讓那些骨頭不再沉默。
”王亞雷忽然說:“我想抓住那個藏尸君。
”蘇天易冷笑道:“你對藏尸君了解嗎?他跟其它的兇手不一樣,我摸不透他的殺人動機。
我剛到總隊就遇上了他,案子擱在那兒兩年了,依然沒有頭緒。
”苗小雨之前聽王亞雷聊起過藏尸君,但也不知其詳,她好奇地問:“既然這般捉摸不透,那會不會是高智商犯罪呀?”王亞雷也說:“是聽說有一類犯罪分子,不按常規套路出牌,表面看到的,都不是真相。
”蘇天易咬咬牙說:“一人連續犯下八起命案,還掐死識破玄機的算命先生,扒光了他的衣服,掛在我們去開棺的墓前銀杏樹上,向我們宣戰,這讓我們整個總隊蒙羞。
”苗小雨問:“算命先生是怎麼識破玄機的呀?”正說著,羅強帶著一個中年男人走進門來,蘇天易輕聲說:“打住,往后慢慢聽我講給你們聽。
”苗小雨見進門的中年男人長得矮胖,頭發稀疏,油頭粉面的,身上的短袖警服還掉了一顆紐扣,一點都不像是刑警大隊長。
羅強介紹道:“蘇法醫,這是我們郭大。
”“蘇法醫辛苦了。
”郭大跟蘇天易握了下手,然后在對面坐下,簡單寒暄了一陣,便切入了正題,郭大說:“蘇法醫,事情是這樣的。
昨天下午,一個村民在浦華江邊沼澤地抓魚的時候,發現沼澤地里有個頭顱。
我們羅強法醫去看了之后,覺得是個兇殺案,事情就這麼簡單。
”蘇天易皺著眉朝羅強點頭示意,然后繼續聽郭大說:“前段時間浦華江漲水漲得很厲害,現在水位退下去,江邊的沼澤地露出來了,也不知道那頭顱是原先埋在那兒的,還是別處漂過來擱淺在那兒的。
”蘇天易轉頭問羅強:“死亡時間如何?”羅強搓搓手說:“我感覺有一年時間了,也不知道對錯,希望蘇法醫接下來幫我們再看看。
”“是男的,還是女的?”苗小雨也問了一句。
“女的,年齡我定不了,反正我感覺死者的年齡不小了,我估計應該過了三十。
”羅強翻開他的筆記本,筆記本上詳細地記錄著他的檢驗分析,字跡鋒利如劍。
蘇天易又說:“哦,我知道了,你說是兇殺案,主要的依據是什麼?”羅強對著自己的筆記本,一字一句地念道:“依據主要來自于損傷,死者頭顱頂部有個很大的骨折破口,我認為那是鈍器打擊形成的。
只是打擊工具形態特殊,我暫時定不下來。
”簡單交流完專業方面的問題,蘇天易就坐在那兒不吭聲了。
郭大見勢說:“蘇法醫,重點還在這個頭顱上,現在不確定的問題還是很多,我們偵查方面需要你幫助再細化了。
找不到尸源,我感覺這案子無從下手呀。
”苗小雨理解郭大的擔憂,無名尸骨要是找不到尸源,案子是辦不下去的,她說道:“郭大,等蘇法醫先看了骨頭再說吧。
”郭大站起身來,曲身從會議桌對面伸過手來,跟蘇天易握了一下,說道:“你知道,我們做刑警的都嫉惡如仇,這案子必須得破。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